
千里江山图(精)9787532183326
正版图书,可开发票,请放心购买。
¥ 46 5.9折 ¥ 78 全新
库存5件
广东广州
认证卖家担保交易快速发货售后保障
作者孙甘露
出版社上海文艺出版社
ISBN9787532183326
出版时间2022-04
装帧其他
开本32开
定价78元
货号31438161
上书时间2024-07-27
- 店主推荐
- 最新上架
商品详情
- 品相描述:全新
- 商品描述
-
作者简介
孙甘露,作家,上海市文联副主席,上海市作家协会副主席,上海靠前文学周、思南读书会总策划。著有《信使之函》《访问梦境》《呼吸》等,作品有英、法、日等多种译文,被收入海内外多种文学选集。他的写作和文学活动,都构成当代文学史的重要组成。
目录
骰子1 龙华14 陶小姐19玄武湖31 身份44 老方52 赛马票69 照片78 诊所88 租客100
远方来信110旋转门123除夕135 暗语145 银行157 皮箱168 茂昌煤号177 二月187
兴昌药号195趟栊门208添男茶楼229茄力克240 后台249 角里259 贵生轮269 公和祥码头280
小桃源290 染坊晒场306 扬州师傅316 墓地326 牛奶棚335 北站344 鱼生粥356 黄浦江366
一封没有署名的信378 附录 材料一 380 材料二 385
内容摘要
1933年,腊月十五,乌云笼罩着上海,一场秘密会议突然被冲,一半与会者被抓。陈千里临危受命,重整队伍,继续执行绝密计划。众目睽睽之下,一场事先张扬的转移险战就此展开……作家孙甘露的最新长篇小说。《千里江山图》从上世纪三十年代的上海,打捞出隐秘而伟大的历史事件,用文学的方式去想象和呈现它的过程。作者捏土为骨,化泥为肉,将散落于历史尘埃中的理想主义者,重新聚起他们的精神和血肉,于焦灼乱世中躬身入局。他们是父亲,是爱人,是兄弟,他们在漆黑的夜里开始一段深不可测的航程。孤寂的至暗时刻,一个人看到什么,愿意看到什么,他就会成为什么样的人。
主编推荐
▼一场事先张扬的险战,一个危险的计划,一部沉浸式烧脑小说,引出一群掩去姓名、藏起过往、躬身入局的理想主义者,他们的激情与勇毅以及爱与别离。
▼激情美学叙事的险峻之作。上世纪三十年代初,在上海、广州、南京的市井街巷,掩映出没着一批理想主义者的身影。孙甘露像拿着一张地图,或像拎着一盏夜灯,带领读者走进现场。不动声色地复刻了一幅幅充满烟火气的生活场景,写出一场场曲折迂回、惊心动魄的生死较量。
▼他们是父亲,是爱人,是兄弟,他们在漆黑的夜里开始一段深不可测的航程。孤寂的至暗时刻,一个人看到什么,他愿意看到什么,他就会成为什么样的人。
▼这个隐蔽战线,也是一个人性纠葛的战场,它塑造英雄,也呈现脆弱。善与恶,罪与罚,贪婪与恐惧,爱与信仰,在小说中得以叠加和蔓延。
▼一部上世纪三十年代的风物志,重现三十年代上海、广州、南京的日常生活,建筑、街道、饮食、风物和文化娱乐,一条马路、一件大衣、一出戏、一道菜抑或一部交响曲。
精彩内容
一九三三年农历新年前后赛马票……风从空旷的跑马场方向吹来,把梧桐落叶吹得到处都是。易君年扔掉抽剩的半根香烟,搓了搓手。两个人一前一后,好像只是不约而同,一起向跑马场方向走去。
跑马场外围的护栏边,行人稀疏,他们停了下来。马赛大多在春秋两季,届时赛道围栏旁簇拥着赌徒和小报记者,人人都争着打听和传播各种真假消息。平常日子,骑师和马夫也会不时牵着马到赛道上转几圈,让赛马在众人面前亮亮相,假装精神抖擞或者萎靡不振,以此操纵赔率。不过这会儿,薄暮笼罩的跑马场上,只有几个外国小孩在争抢一只皮球。
“陈先生对什么感兴趣?我只懂点字画。”“那我就找对人了。”皮球踢上半空,又落到砂石赛道上,惊起几只麻雀。陈千里轻轻地说:“我只担心买到假货。”“买到假货,那是常有的事,在上海,连金先生这样的大藏家也不免上当。”围栏边突然孤零零出现一匹赛马,马背上盖着条纹毛毯,马夫远远跟在后面,不时吆喝几声。一马一人寂寞地在赛道上绕着圈。
“愿闻其详——”在冬日黄昏的萧瑟寒风中听一个略带喜剧性的故事,陈千里对此似乎很有兴致。
“金先生最爱明四家,做梦都想要一幅‘仇英’,字画行里是个人都知道这件事。”易君年又点了一根香烟,盯着那群正翻过围栏、准备回家的小男孩:“于是有一天,‘仇英’自己上门来找他了。来人说,手上有一幅‘仇英’的小画。金先生喜之不尽,约定日子让他拿来看,还特地约请了沪上一位书画界的行家,于那日一起来鉴赏。
“到了那天,此人果然拿着一幅‘仇英’上门,请来的那位行家细细观摩了好一阵,然后说,这幅画是假的——”易君年停下来,抽一口烟。
“既然是假的,以金先生的身份地位当然不收。金先生也不多话,客套了一番后,礼送出门。那位行家也婉辞夜宴,一同出门离去。
“金先生有点奇怪,多生了个心眼,让下人跟着出去,正看见这位行家在门外街上拦着来人横竖要买。下人回来报告金先生,金先生大怒,这快赶上明抢了。第二天金先生就让人捎了一句话给那位行家,要么卖给金先生,愿意再加价一倍,要么自己拿着那幅‘仇英’,从此就别想在上海滩混了。”“那幅画是假的。”陈千里说。
“正是如此。”易君年扔掉烟蒂,“那位行家自己画的。”陈千里忽然笑了起来:“故事是好故事,可这故事像是从《笑林广记》里偷来的。”他从大衣内取出一册广益书局版《笑林广记》,递给易君年。易君年接过去翻开,书中夹着半张跑马厅大香槟票。
“这回大香槟赛,开出头奖二十万。”易君年一边说,一边往怀里掏,“赌马的人越来越多了,市面越是萧条,跑马场就越热闹。”他掏出半张马票,上印“提国币一元作慈善捐款”。他把那两个半张合到一起,凑成完整的一张。
……趟栊门……她在等他解释,但他领着她下楼。她每下一阶楼梯,就感觉自己又朝黑暗的水底沉下一截。
“这地方太黑了,什么都看不见。”凌汶说。
易君年明白凌汶的弦外之音:“我做过许多事,每做完一件事情,我就把它锁进一个没有窗户的房间,就像这间。你以为龙冬不是吗?我和他做的事情没什么两样,他顶多比我多了一样共产主义。你能看清他吗?你能找到他吗?我领你去看。”凌汶在黑暗中停下脚步,震惊地望着对面这个人形,本能地往后退了一步,易君年一把拽住她,把她拉进了底楼后面的尾房。那间没有窗户的巢穴背后是厨房,灶台一角裂开了,铁锅里有几片枯叶,两块碎砖。厨房后墙上有一扇门,易君年打开门,外面也是一片黑暗。
易君年转过身来,面对着凌汶:“龙冬能跑到哪里去呢?他面前只有这一条路,对你我来说也一样,到处都是黑暗。”易君年在七姑门前站立片刻。七姑睡醒了,在房间里来来回回不知道在找什么。他想了一会儿,撕下一片门联,擦了擦手上的血。
天官里后街上没有光,也没有人。易君年刚转进朝北的直巷,突然听见身后有人说话。
他转身,墙角有半截人影。易君年没有说话。
声音又起,是那个算命的老头。
“你在跟我说话?”他问老头。
“你怎么一个人出来了?那位太太呢?”他没有回答,望着那截影子。过了一会儿,易君年又问:“你想说什么?”“我一直在等你,刚刚你们急着过去,话还没说完。那首签诗,后面还有两句没写。”“你说。”易君年朝他走近了一步。
“借问东邻效西子,何如郭素拟——”老头拉长着声音吟诵,还没等他念完,易君年闪身靠近,伸出双手掐住了他的喉咙。
易君年叠齐那双了无生气的手臂,又把算命人的头颅端端正正放在手臂当中。
后台乐华不远,维新路朝南到西湖路,向东一转,再走到下一个街口,就看见骑楼下面戏院的大招牌。当晚戏单上果然有小凤凰,是《十美绕宣王》之“背解红罗”一本,小凤凰演的正是苏金定。
等到天黑,陈千里和梁士超买了票子,提前进了戏院。还没到开戏时间,中间的桌位都空着,两侧坐席倒来了不少人。他们早就换了衣装,这时一个长袍马褂,一个浅色洋装,一副洋行买办形貌。两人并不立即入座,从廊柱后面走到台下,陈千里示意梁士超在外面等着,自己推开角门走了进去。
后台门前坐着杂役,正要问,陈千里摸出一块银元塞进对方手里,直截了当说一句:“去看看小凤凰。”戏院后台常有豪客进来,指明想见某位某位,戏院中人不以为异。那人收了银钱,不曾想戏未开演,已收了红包,心里十分欢喜,告诉陈千里:“小凤凰在楼上。”上楼梯就有一股脂粉味。群芳艳是女班,后台莺莺燕燕。上面一条楼道,两个人并肩嫌挤,两侧房门半掩,里面传出嘁嘁喳喳说话的声音。陈千里站在楼道中间,轻松地大声说:“我找小凤凰。”“谁找我?”一扇房门从里面打开,勒眉贴片,只上了片子石,未戴凤饰,身上已穿了金红广绣戏服。烟铺黎叔说她鬼火咁靓,这会儿却看不出来。
陈千里走了过去,笑着说:“我。”进了门,他又说:“鄙姓陈。”小凤凰疑惑地看着他,进后台的客人,一定常常来戏院,她在戏台上早就看熟了。来人身材高大,目睛闪闪,浑不似平日所见那些膏粱纨绔,心中不由一顿。
“还没看戏,陈生就想来看人了。”她也笑着回了一句。
陈千里拿出银烟盒,弹开盒盖,自己拿了一支,又将烟盒递到小凤凰面前。小凤凰伸手拿烟,忽然发现香烟是茄力克,愣了一下。
“我替一个朋友来看看你。”……小桃源高墙下却是一道黑漆窄门,门楣匾额上书“小桃源”。进门是个园子,种着二三十棵桃树。宾客通常进门后才知道,偌大园子,只有那一道窄门,业主早就筑墙封了其他各门。旧城人烟密集,却有这么一处占地半亩的园子,颇有几分新奇。
墙内悄无声息,叶启年踏上三级石阶,轻扣了两下铸铜门环。过了一会儿,门开了。
“孟老,启年给您拜年了!”叶启年拱了拱手。
门内孟老,穿一件旧棉袍,他并不讶异,似乎猜到来人是叶启年。
“我就知道这时候来客,多半就是你。”园中有几间平房,房前砖地纤尘不染,青苔错杂,墙边蓄水石槽中浮着几叶铜钱草,厅里一几两椅,有只黑猫躲在几案下,并不看来人。
“来得正好,我刚沏了茶。”“一向还好吧?”叶启年淡淡地问道。
“拜老弟所赐,借我一个好地方了此残生。”孟老寒暄道。
阳光照在厅前地上,滚水注入壶中,茶香盈满室内。
“孟老还是那么客气,这是请你帮我照看房子。”叶启年当年从川军一个下野师长手里购得这园子,从黄泥墙迁来几十棵桃树,如今这些桃树大隐于市,竟成了绝版。他虽然住在南京,这些年来只要有空,就会悄悄跑到上海,来到小桃源,找这位孟老喝茶说话。
孟老杀过人。十多二十年前,在一些激进社团里,他是赫赫有名的刺客。
两人没有过多寒暄。茶冲了几回,叶启年忽然开口说道:“我没有亲手杀过人。”碗盖叮当,孟老放下茶碗,略感诧异。面前这位老友,相识多年,虽然往来说不上频繁,但似乎无话不谈,孟老心思缜密,谈古论今也是点到即止。“小桃源”是个避世之地,惯常往来只是饮茶闲聊,求一时清闲,此番开门见山忽然谈及杀人,令他有些疑惑。
“这一回我下了决心。”叶启年的声音在寂静的宅院内显得有些刺耳。
“像老弟这样身居高位之人,杀人何须亲自动手。”孟老一时不知如何接话。他杀过人,却从不谈论杀人。
叶启年望着庭前光影下的桃树,没有理会孟老的话。他豢养过许多人,却从来不明白自己为什么要豢养面前这个老头。也许他需要这么一对耳朵,也许他觉得只有这个老头能听明白他的意思。
……一封没有署名的信(龙华牺牲烈士的遗物)我一直想给你写一封信,但是不知道怎么落笔才不会泄露。
也许该用密写的方式写在纸上,或者用莫尔斯电码编成一段话,但是所有这些方式,都只是试图在万一被发现时无法破译。而我真正想对你说的并非秘密,可以写在云上,或者写在水上,世间任何人都可以看到,但那只是写给你的。犹如我此生说过的所有的话,被你的眼睛、耳朵捕获,像是盲文或者世界语,它的凸起,它对自然语言的模仿,那隐约的刺痛或者句法,为你的指端所记取。
我从来没有想过我们会分别。虽然,每分每秒都可能是我们永别的时刻。而如果我们能看着彼此分开,那已经是幸运了。
你大概读不到这封信,我也许已经不在了,已经离你很远,在某个我不知道的地方。
我不知道我应该在哪里等你,你才能找到我。但你会知道的吧?
我们并不指望在另一个世界重聚,我们挚爱的只有我们曾经所在的地方,即使将来没有人记得我们,这也是我们唯一愿意为之付出一切的地方。
我爱听你讲那些植物的故事,那些重瓣花朵,因为雄蕊和雌蕊的退化与变异显得更为艳丽,而那些单瓣花朵的繁衍能力更强。
什么时候你再去龙华吧,三四月间,桃花开时,上报恩塔,替我再看看龙华,看看上海。还有报恩塔东面的那片桃园,看看那些红色、白色和红白混色的花朵。
我们见过的,没见过的。听你讲所有的事,我们的过去,这个世界的未来。
有时候,我仿佛在暗夜中看见了我自己。看见我在望着你,在这个世界上,任何地方,一直望着你,望着夜空中那幸福迷人的星辰。
— 没有更多了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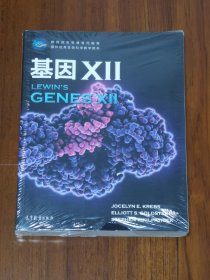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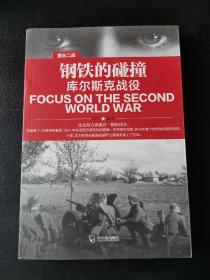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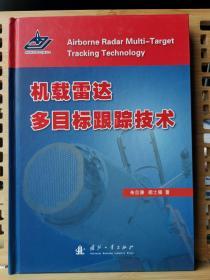











以下为对购买帮助不大的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