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肥沃的黄河滩
正版图书,可开发票,请放心购买。
¥ 67.7 7.6折 ¥ 89 全新
库存30件
广东广州
认证卖家担保交易快速发货售后保障
作者段艾生|
出版社作家
ISBN9787521225709
出版时间2024-04
装帧其他
开本其他
定价89元
货号32035441
上书时间2024-06-07
- 店主推荐
- 最新上架
商品详情
- 品相描述:全新
- 商品描述
-
作者简介
段艾生,中共党员,大学文凭。1960年出生,山西新绛县人。当过农民、工人、教师、军官、法官。1978年参军入伍,1988年转业到山西省高级人法院院工作。先后在报刊媒体发表杂文、散文、中短篇小说及新闻报道、理论文章一千余篇。中国经济出版社2006年出版《创业者的52个黄金理念》和《创业者的100个误区》两部专著。其中《创业者的100个误区》被中宣部等九部委列为全民读书推荐书目。
内容摘要
黄河岸畔的北韩村,风雨飘摇一百年,几经兴盛衰败,村民在不屈不挠的反抗和英勇顽强的抗争中,在数不尽的坎坷和挫折中,最终盼来了好日子。钢筋铁骨,正直的韩成根;奋发读书,矢志不移的韩石山;聪明反被聪明误的韩六娃;心胸狭隘,睚眦必报的韩黑虎……长达一百年的村史变迁,是黄河儿女倔强不屈、薪火相传、源远流长的悲壮史话。
精彩内容
\"一
韩成根侍弄庄稼行,但侍弄女人不行。他拢共娶过三个女人,却没能结出一粒果实。
头一个女人娶的是杨家圪垴杨三的大女儿梅梅。他那时才十三岁,而她已经十九岁。她是他在男女之事上的启蒙老师,也是他一辈子都未能愈合的心灵伤疤。
成亲那天,他在大人们的摆弄下懵懵懂懂娶回了她。席摊子一散,洞房里就剩下了他和她。
头一回和一个女人单独待在一间屋里,如同把他和老虎关在一个笼子,吓得他脑瓜子上直冒汗,心窝里就像有只兔子,扑腾扑腾直往嗓子眼里圪跳。他低着脑袋坐在炕沿上,两只手不停地搓动,掌心里的油腻被搓成一根又一根的黑泥条。
过了一阵,她轻轻地说:“咱们睡吧。”他连看都没敢看她一眼,就日里慌张地脱光衣服,吱溜一下钻进被窝,连脑袋都不敢露出一点儿。
又过了好长好长一阵儿,她伸过手一把把他拽进她的被窝,搂进她的怀里。一股他从未闻过的女人特有的味道窜入他的鼻眼里。她摸他的背,摸他的尻蛋子,摸他自穿上合裆裤就从不让人随便看的地方。
“这是啥?”她问他。
他慌慌地说:“雀雀。”她又问:“天黑了,雀雀为啥不钻窝?”他说:“哪儿有窝?”她就牵着他的手,引到她穿上合裆裤更不让人看的地方:“这不是?”她一边说着话,一边就把他的小雀雀引进了她的窝窝里。
又待了一会儿,她躺在他的下面说:“你咋的不动弹?”他嘿嘿笑道:“这里面还挺暖和的。”她说:“你没看见雀雀一会儿进窝一会儿出窝吗?”他说:“见是见过,可不知道咋个进法,咋个出法?”她说:“我说雀雀进,你就进;我说雀雀出,你就出。”于是,他在她的引导下,反反复复地进,反反复复地出。忽然,他浑身汗渍渍地趴在她的身上不动弹了。
她说:“你咋又不动弹了?”他红着脸不好意思地说:“雀雀屙到窝里了。”第二天早上,她把他从睡梦中推醒。
他用手背揉了揉糊在眼圈上的眼屎,迷迷糊糊地问:“咋哩?你又要咋哩?”她笑着说:“咋哩?你说咋哩?日头都晒到尻子上了还不起来?”他朝窗户一看,太阳早都爬到了房顶上。他赶忙穿上衣裳,手脸也不洗就趿着鞋往饭厦跑。夜里闹腾了半宿,他早饿得耐不住了,端起饭碗就呼噜呼噜大口大口地吃喝。
填饱了肚子,他拿手抹掉嘴边的饭渣,一抬头看见她正笑着拿眼睛瞄他,腾一下脸就红了,傻乎乎地就冒出一句愣话:“笑?哩?夜黑儿扳得我尻子这会儿还疼!”他爹听了,狠狠地瞪了他一眼:“这娃,胡说啥哩!嘴里连个把门的也没有?”他爹虽然嘴上日砍他,但心里却很熨帖:扳得好!扳得好!不扳你你晓得爹给你费劲巴事地娶媳妇做啥?不扳你你狗小子能成了真正的男人?不扳你人家梅梅能迈过从姑娘到媳妇的坎儿?
韩成根这句愣话,消除了他爹韩耀祖积存了很久的一块心病。夜儿个黑里,韩耀祖还担心成根心憨,梅梅害羞,让成根枉担了娶媳妇的名儿。总管韩六娃昨儿个醉醺醺地对着他的耳朵问:“给娃请襻裆吗?”“襻裆”是这一带的土话,意思相当于队伍上的教练官。大户人家时兴给娃子娶大媳妇,小娃子不懂娶媳妇做啥,就请个做过这号事的男人教娃子。
韩耀祖原本也想给成根请个襻裆,但一寻思头年韩虎儿的娃子韩狗蛋弄下的那桩丢人事儿就改变了原先的想法。
狗蛋年头里娶了一个比他大半轮的女人。他爹韩虎儿怕他懵懂,就请了刚娶过媳妇的韩三三给狗蛋当襻裆。狗蛋笨得咋教也教不会。三三就说:“笨死啦!你看,就这样。”说着,就自个儿上到羞得把被子蒙在脸上的狗蛋媳妇身上,给站在一旁的狗蛋示范了一遍。
第二天,狗蛋把这事儿给韩虎儿学说了一遍,韩虎儿听了半截,就抡起锄把把狗蛋打得一瘸一拐,一半个月都走不成路。打完狗蛋,韩虎儿又掂起锄头找到三三家。见了三三,韩虎儿二话不说,抡圆了膀子就把锄头往三三的脑袋上砸。三三自知理亏,抱住脑袋就跑。
三三爹弄不清咋回事,一边夺锄头一边问:“这是咋啦?这是咋啦?”韩虎儿黑着脸不搭话,丢下锄头就追三三。
三三日急慌张地往院门外面跑,被门槛绊了个狗啃屎。
韩虎儿追上去,一边“日死你先人,日死你先人”地胡吷乱骂,一边朝三三身上没头没脸地狠命踏了几脚。
三三从地上爬起来,正要从韩虎儿拳脚轮击中挣脱出来。韩虎儿急了,抱住三三在三三脸上啃下一块血淋淋的肉。
三三爹赶上来使着浑身的劲儿掰韩虎儿的手,三三娘也赶来把三三往一旁扯。
韩虎儿临丢手时,又抓住三三的头狠狠地揪下了一绺带着头皮和血迹的头发。
一想起这事,韩耀祖就有一种利刀剜心的感觉,生怕狗蛋的事再发生在成根身上。所以,六娃夜儿个一提请襻裆的事,韩耀祖就连忙又是摇头又是摆手:“不请,不请。咱娃心眼灵灵的,请那做啥!”娶过梅梅的头一年,成根一家倒也过得平平安安、和和美美。但一闪过年,他爹就开始渐渐地给梅梅脸子看,动不动不是摔碟子摔碗,就是骂牲口骂鸡。梅梅一开始也没把这事放在心上,但日子一长,梅梅就觉么到公公的脾气全是冲着她来的。每回公公冲她使完性子,她总要背过弯躲进自个儿的屋子里偷偷哭一回。她知道公公之所以给她使性子、甩脸子,是嫌她肚子总是瘪瘪的不给他怀孙娃子。
养鸡为了下蛋,播种为了留后。天底下哪个老人费劲巴事地给儿娃子娶媳纳妻,可不是光图了让你和人家儿娃子行皮肉之乐,终归是要你给人家传宗接代、延续血脉。对于这一点,梅梅理解公公的急切想望和迫切心情。可这怀胎生娃也和耕地播种一样样的,光有肥沃的土地不行,还得有饱满成熟的种子才行呀。成根还是个没有长成的奶娃子,有没有下种的能力都很难说,她的肚子里怎么可能凭空生出来胎芽芽?两个人才能弄成的事,凭啥就把棍子往我一个人的头上打?
看见梅梅背地里泪儿泪儿地哭,韩成根就劝梅梅:“你别和他一般见识,咱爹就是这号 脾气。只要咱俩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终究会熬到秋收那一天。”听了成根说的宽心话,梅梅一口气把灯吹灭。两人迅即铺褥展被,脱衣褪裤,纵横连合。
此后的日子,成根爹虽然常和梅梅怄气,但小两口儿却从未红过脸、拌过嘴。对韩成根来说,梅梅给他的爱、给他的情,就是来生来世也忘不了。
韩成根之所以一辈子忘不了梅梅,不仅仅是她做了他初尝人间欢爱的启蒙老师,更重要的是她给了他从未体味过的母爱。他还不会叫娘的时候,他娘就得了痨病,无奈地撇下他到了另外的一个冰凉世界。直到他娶过梅梅,还有尿炕的毛病,这使他在村里的小伙伴们跟前抬不起头。梅梅天天夜里叫他起来尿尿。有时候梅梅累了睡得沉顾不上叫他,他不小心尿了炕,梅梅就不声不响地用自己的身子悄悄暖干。他夜里尿完尿老肚子疼,梅梅就用手给他揉,就拿她的肚子暖他的肚子。至于浆洗缝补、吃吃喝喝的事儿,就更侍候得他说不出半点儿不是。好多时候,他都差点儿忍不住喊她一声娘。记得他十四岁那年的秋天,他割猪草时被蛇咬了一口,梅梅看见了,就趴在他的腿上用嘴把蛇毒吸了出来。他没事了,但梅梅却头晕得好几天躺在炕上起不来。
秋天是收获的季节,但不是每个人都有收成。韩成根和梅梅经过几年的不懈努力,虽然经历了好几个秋收时节,但却在生娃这件事上连个胎芽芽也没努出来。
韩成根十八岁那年的三伏天之后中秋节之前,和他共同努力了三千六百多个日日夜夜的梅梅终于离开了他,在他心里留下一块流了一辈子血的伤疤。
这事他一点儿也不怨梅梅,全怪他那脑子眼糊涂得像一盆糨糊的爹。他和梅梅过了几年,梅梅的肚子总是平展展的,没有一点儿要开怀坐胎的兆头。他爹眼巴巴地盼了几年孙子没盼上,就一股脑儿地怨梅梅,就要把梅梅休了。他向他爹说:“这事咋能光怪人家?弄不好过几年就好了。”“不怪她怪谁?人家比她早嫁人的也有,晚嫁人的也有,都是肚子下头一个挨着一个的扑当扑当下崽娃。人家有的女子进了别人家门、上了别人家炕,当年开花、当年挂果、当年娃崽就吊在了奶头上。她倒好,展展过了六个年头,从下月初一到腊月三十,从年顶顶上到年根根上,任凭日落月升,任凭春去秋来,寸草不长,颗粒不生,分明是一个不下蛋的二混子草鸡、不下驹子的三混子母骡。”韩成根爹指天指地、指鸡指马,吹胡子瞪眼地发泄心中的愤懑。
韩成根心想:梅梅生不下娃崽,也许根蔓在梅梅那里,也许根蔓在自己这里,也许是他和梅梅生子传后的缘分未到。这样糊里糊涂怪罪到梅梅一个人头上,那梅梅不是像岳飞一样没有缘由地顶了“莫须有”的罪名。
“也许不是梅梅的过。让梅梅留下再等等看。”韩成根带着几分乞求地看着他爹。
他爹立时把眼睛瞪得比卵子还大:“往哪里等?等到我咽了气闭了眼?等到我装进棺材里埋到土里头?”不晓得咋搞的,爹的话竟传到了十几里外的杨家圪垴。老丈人杨三儿听说后,当下就风风火火打上门来。
他爹韩耀祖脸红脖子粗地说:“你有啥脸找上门来。你不知道你家女子是块不长庄稼的盐碱地?”“呸!”杨三儿狠狠地啐了一口痰,指着韩耀祖的鼻子说:“放屁!你拿秕谷往地里撒能出苗吗?你家的底子你不清楚?!”杨三儿的话就像一块冷黏糕一样,噎得韩耀祖半天干张嘴说不出一句话来。
韩家三代单传,村里村外早有他家男人不行从外人那里借种的传言。
如果杨三儿当时闹到这一步罢手的话,梅梅还不至于离开他,偏偏杨三儿是个得理不饶人的货。闹完之后,就胁唬着把哭得眼睛肿得像核桃一样大的梅梅弄回了杨家圪垴。
几个月后,在家里一手遮天的老爹连问都没问他,就托人给他说下了刘家沟的刘虎子的三姑娘红果。
他勾着脑袋对他爹说:“爹,这事你别忙活了,我这辈子再也不娶了。”他爹把烧得红红的烟灰磕到鞋底上,用滚烫的烟锅在他脑门子上狠狠地敲起了一个血疙瘩:“这是爹的事,用你瞎操心?”他一声不吭从屋里退出来,扛起锄头就往他家那块紧靠河边的滩地走。碰上人和他打招呼,他也不搭理。
在村巷里正赶着羊往滩地里走的韩茅勺拦住他笑嘻嘻地问:“成根,你干啥去?”他头也不抬就甩过去一句:“锄地去!”“大冬天地里啥也没有你锄啥?”韩茅勺眊着把脖子梗得像镢把似的韩成根哂笑道。
韩成根凶凶地瞪着眼吼道:“管老子锄啥?锄你娘的腿板子去!”韩茅勺望着走远了的韩成根,嘴里咕哝道:“这 娃今天疯了。”进了腊月门,风里面就有了割人的刀子。平日不耐冻的韩成根却一点儿也没感觉。河边的风刮得很大,天上的鸟雀被吹得歪歪斜斜,努着全身的劲儿才能勉强控制住飞翔的方向。滩地的柳树东摇西晃,发出呜呜的哭声。韩成根觉得自己很像天上的鸟雀,不知道将要被刮到什么地方;又像身边的柳树,不知道将要被揉搓成什么样子。在自己的婚事上,他的确像他爹说的那样,自己管不了自己。这不光是他一个人是这样,祖祖辈辈的人都是这样,满世界的人都是这样。哪个做老子的不是把儿子娶媳妇的事当成自己的事来办?哪个做儿子的娶媳妇能由得了自己。他很想梅梅,好多次做梦都梦见了梅梅。他梦见梅梅又回来了,梦见梅梅又和他睡到了一盘炕上,还梦见梅梅给他生了一个和他一个模子里脱出来似的黑小子。他真想把梅梅再接回来,真想再钻进梅梅每天给他暖得热烘烘的被窝里,真想再投进梅梅那满是奶香味的棉花一样的怀里。他不敢跟人说,更不敢跟爹说。他只能睁着眼睛对天想,只能闭上眼睛在梦里想。可梅梅对他来说,只能是镜子里面的一朵花,只能是河湾里面的一弯月,只能是心中一块永远流血的伤疤。
正月初六,韩成根带着他心中的梅梅,带着他流血的伤疤,娶回了他极不情愿的第二个女人——红果。
办事那天,韩成根像个木头人一样,执事总管韩六娃叫换新衣裳他就换新衣裳,叫他骑上马去接亲他就骑上马去接亲。
韩六娃拍拍他的尻子说:“不要像木头橛子似的硬硬地戳着,脸上喜欢着。”他强按下心中的不快,努着劲笑了笑,结果笑得比哭还难看。
他爹见了,就跑到跟前说:“你狗日的,人家都欢欢喜喜地来给咱帮忙,你个丧门星给谁甩脸子?”韩成根眊了他爹一眼,把脖子一梗,把脸扭到一边。
他爹火了,嘴里也就没了好话:“我看你狗日的今天是脑袋上顶驴?,本事大得要日天哩!”说着,就脱下鞋子要拿鞋打他。
韩六娃连忙拉住:“不敢这样,不敢这样。其实成根挺喜欢的,我是故意逗他哩。”一帮帮忙的乡党围过来劝解,把他爹往一边推。
韩六娃高声喊道:“好了好了,大家都高兴着。”接着,又脖筋暴突地扯开嗓门长长地吆喝一声:“起身——”“走了——”接亲队伍应着韩六娃的号令,嘻嘻哈哈拥着韩成根出了院门。
韩成根心里本来就不顺和,让他爹这么一弄,就越发不痛快了。他憋着气,黑着脸,好像谁欠了他二百六十吊银钱似的。
韩六娃在路上一边走一边劝,好话说了一河滩,但韩成根脸上终究也没露出一点喜欢劲儿。
到了丈人家,韩六娃叫他叫丈人叫爹,他就木木地叫一声爹;韩六娃叫他叫丈母叫娘,他就木木地叫一声娘。坐席的时候,韩六娃叫他吃菜他就吃一口菜,叫他喝酒他就喝一口酒。吃了喜面,韩六娃叫他把红果抱到马上,他就铁青着脸把红果像抱木头一样抱起来,“咚”的一下扽到马背上。
韩六娃见韩成根不听人劝,就闭住嘴再也不言烦了。
把红果接回来后,韩成根仍然像木头人一样,韩六娃让他拜天地,他就木偶似的拜天地;韩六娃让他拜高堂,他就木偶似的拜高堂;韩六娃让他与红果对拜,他仍像木偶似的与红果对拜。直到进了洞房,他仍像铁棍子似的杵在炕沿上。
十三岁的红果满身奶胎味,一脸娃娃气。让人摆弄了一天,身上早乏得没了精神。见人走光了,也不管成根的脸好看难看,自个儿脱光衣裳就钻进了被窝。不过半袋烟工夫,就呼噜呼噜跑到梦州国里了。
过了三天,红果的哥哥接红果回门,红果胡乱拨拉了两口饭嘻嘻笑笑跟着走了。又过了三天,成根爹让成根把红果接回韩家。
韩成根寻思了几天,心里也慢慢转过了弯。梅梅没一点想望了,老和红果打别也不是长事。昏暗的油灯下,他瞄了一眼红果,猛然发现胎味还没褪尽的红果并不比梅梅差到哪里。他撩起衣襟把油灯扇灭,一下把红果搂到怀里死死地抱住。
红果吓得叫喊:“你要干啥?你要干啥?”韩成根不言声,用长满硬茧的手脱红果的衣裳,摸红果的下身。
红果使劲推他,但推不动,带着哭腔说:“你这是做啥?你这是做啥?”韩成根把嘴贴到红果耳朵梢上说:“我想敌你哩。”红果听了,就哇哇哇地大声哭了起来。
韩成根见硬来不行,就松开手想给她说软话。没想到红果紧紧地抱住胸口,一阵风似的跑回了娘家。
红果头发乱糟糟地跑回家,把全家人都吓呆了。
红果娘脸色煞白,一把把她搂进怀里:“咋啦,谁欺负我娃了?”红果委屈地哭了一阵,就把事情原委说了一遍。
她爹和她娘听了她的述说,舒展开圪蹴到一堆的眉眼,虚惊一场地松了一口气。
她嫂子扭过头,捂着嘴偷笑。
她爹对她娘和她嫂子说:“这是女人们的事,你们劝劝她,一会儿让她哥把她送回去。”说着,端着烟杆就走到另一厢房里。
她娘叹了口气,眼里落下几滴浑浊的泪:“女人呀,天生的受罪坯子。小的时候比男娃们矮半圪节,嫁了人要受男人的摆弄,老了还要伺候了大的再伺候小的。你不让成根……”觉得后面的话不是当娘的能说出口的,就看着她嫂子说:“你把道理给她说道说道。”说完,就扭着小脚也跑到另一厢房里。
她嫂子拉着她坐到炕沿上说:“妹子,你不懂,成根那样不是欺负你,他是爱你哩。”红果说:“那也不能脱人家的衣裳,在人家身上胡摸呀?”她嫂子笑了:“你真是个憨憨,那就是成根爱你哩。男人爱女人都是这样爱法。”红果疑惑地问:“嫂子,你哄我哩吧?”她嫂子板了脸说:“嫂子是过来人,嫂子还哄你?男人头一回爱的时候,女人都害怕。头一回过去了,后面就不怕了,时间一长,女人倒还想让人家男人这样哩。”红果不好意思地低下头说:“那我哥也是这样爱你?”她嫂子脸上也红了,朝红果“嗯”了一声。
“那我哥也是他那样,又脱衣裳又胡摸?”红果又问。
她嫂子脸红透了:“不是这样又是哪样?”天亮前,红果跟着她哥回到了韩家。
韩成根本来打算丢下心里的梅梅和红果好好过日子,但红果半夜出走的举动,一下又把他的倔圪揽脾气惹犯了。红果哥把红果送到他跟前,他梗着脖子铁着脸冷冷地说:“有本事跑,就有本事别回来!”红果哥红着脸说:“红果还小,还不懂事,家里老老小小说了她好半天才把她劝回来。我走了,人给你留下了。”韩成根说:“留下干什么?昨天咋走的今天还咋走。”正说着,他爹端着烟锅进来说:“回来就好,回来就好。我今天还说让成根去接哩。麻烦她哥给送回来,真让人不好意思。成根,还不快给你哥倒茶?”说着,就给成根递了个眼色。
韩成根只当没看见,把脸扭到一边:“倒茶可以。但咱得把话说清楚,人我是不要了。”他爹火了,打雷似的吼道:“由了你了?只要老子不咽气,家里的事就得由我做主!再给我胡说,看我不把你的狗腿打断!”韩成根气呼呼地说:“留下她可以,让龟孙子和她过去!”说完,噔噔噔走了出去。
韩成根前脚走出院门,红果后脚就跟着捂住脸哭着跑回了刘家沟。
他爹眼巴巴地看着送回门里的儿媳妇又被成根给呛回去了,一下气得发了疯似的从门后面捞起一根胳膊粗的柳木橛子满村子找韩成根。
他爹一边在村子里找韩成根,一边瞪着血红的眼珠子连喊带骂:“成根!成根!你躲到哪里了?你有本事你回来,老子今天不把你的狗腿打断就不是人!”韩成根听人说了,吓得躲在外面一天一夜没敢回家。
第二天早上,他觉得爹的气消得差不多了,才浑身圪圪颤颤地往家里走。
没想到,爹把院门关得死死的。
他不敢敲门,更不敢喊爹开门,悄悄翻过院墙进了院里,做贼似的往马棚里溜。
展展一夜没合一眼的爹见成根往马棚里钻,忽地站起来,提起木橛子就扑了上去。
韩成根吓毛了,慌忙收紧皮肉站在那里等着挨揍。
他爹扑过来抡起木橛子就朝他身上乱打一气,一边打一边骂:“我让你驴日的倔!我让你驴日的跑!我让你驴日的本事大得日天去!”韩成根站在原地也不动窝,也不遮挡,任凭爹的木橛子暴风雨般地打来。
他爹见他也不挡也不护,只是用一双不服气的眼睛反瞪着,窝在肚里的气就越发大了,手里的木橛子专门朝他腿上打:“我让你犟!我让你硬!我让你硬邦邦地再给我顶!”几下下去,就把韩成根打得趴在地上不能动了。
他爹丢下木橛子,弯下腰哆哆嗦嗦地指着成根的脑袋问:“说!还给老子耍不耍犟?”韩成根死死地咬住牙不说话。
“说!你给我把红果接回来不接回来?”他爹颤动的手指都快要戳到他的脑门上了。
韩成根闭住眼,不言声。
他爹见他不服软,不回话,气得又拿起木橛子打,打一阵又问:“说!你给我把红果接回来不接回来?”不管他爹怎样打怎么问,韩成根自始至终不说一句话,不点一下头,硬圪橛橛地杵在他爹脸前。
他爹气得没法,丢下木橛子杀牛般地吼道:“给老子跪下!多会儿不犟了再给老子起来!多会儿愿意接红果了再来见老子!”韩成根跪在院子里,被毒毒的日头晒得一身一身地出汗。
他爹木棍似的坐在炕上,一锅一锅地抽烟。
日头快挪到天空当间的时候,韩成根一头栽倒在院子里。
他爹舀了一瓢凉水,浇在他的头上,扭过身走回屋里坐在炕上又抽开了烟。
尽管他爹拿木橛子把他的腿给打断了,但韩成根却宁死也不和红果过了。
他爹管不下他,气得一病不起。正月根上,他爹带着没能在自己手里给儿子最终娶妻成家的终身遗憾、带着后继无嗣愧对列祖列宗的愧疚、带着对儿子不服管教的满腹恼恨离开了阳世。
死的时候,他爹眼睛一直瞪着,怎么也不肯闭上。
韩成根虽然哭得死过去两次,却终归没有给已经咽气的爹服软回话。
丧事总管韩六娃急得没法,只好把韩成根撵出去,对直挺挺地躺在炕上的韩耀祖说:“耀祖叔,你放心地走吧,侄子我一定给成根弄回个让你称心的媳妇,一定让成根给你早日生子传宗。”说完,就用手去抹韩耀祖的眼睛。韩耀祖这才闭上了怎么也不肯闭上的眼睛。
七天之后,早已长眠在村后老虎沟的成根娘的坟堆,被村里人用铁锹和铁镐刨开,把成根爹放进去合葬到一起。
\"
— 没有更多了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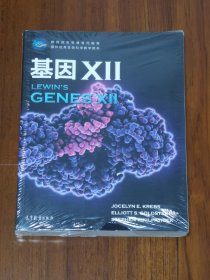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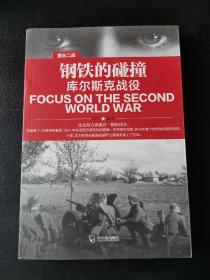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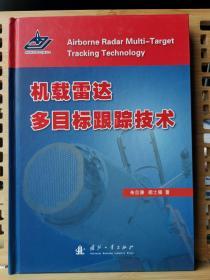











以下为对购买帮助不大的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