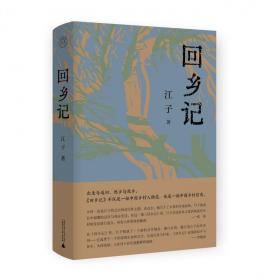
回乡记
正版图书,可开发票,请放心购买。
¥ 26.75 5.4折 ¥ 49.8 全新
库存4件
广东广州
认证卖家担保交易快速发货售后保障
作者江子
出版社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ISBN9787559845221
出版时间2021-12
装帧精装
开本32开
定价49.8元
货号31346728
上书时间2023-09-12
- 店主推荐
- 最新上架
商品详情
- 品相描述:全新
- 商品描述
-
作者简介
江子,本名曾清生,男,1971年7月生于江西吉水。中国作家协会会员,现居南昌,供职于江西省作家协会。著有《青花帝国》《去林芝看桃花》《田园将芜——后乡村时代纪事》《苍山如海——井冈山往事》等。获《北京文学》《作品》刊物奖、第二届孙犁散文奖双年奖、第三届江西文学艺术奖、第七届鲁迅文学奖提名等奖项。
目录
第一辑 出走
练武记
行医记
购房记
怀罪的人
不系之舟
临渊记
第二辑 返回
磨盘洲
杨家岭的树
回乡记
建房记
第三辑 他乡
高考记
三叔家的狗
指上的航行
明月此时(代后记)
内容摘要
作者江子出生于赣江以西,曾经出版过乡村主题专著《田园将芜》引起过较大反响,而这本《回乡记》就是《田园将芜》的续篇。《回乡记》以吉水赣江以西区域的历史与现实为研究对象,全面田野式考察农民进城、传统留存、异乡与故乡、出走与返回、新乡贤的责任与命运等,以图全息呈现一块经典乡土的历史与现实,为当下的乡土中国留一份证词。中国现在为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期,这种变局,乡村的变迁是其标志。江西是农耕文明最有代表性的省份,通过书写新的历史节点江西乡村的常与变,可以解码当下中国。
主编推荐
《回乡记》作者江子,中国作家协会全委会委员,出版过散文集《青花帝国》《去林芝看桃花》等作品。该书是以吉水赣江以西区域的历史与现实的记忆为基准,全面记录了新时期环境下的农民发展的进程,传统与现代,异乡与故乡,出走与回归等多层的农村地域文化尽现眼前,从而展示了一个小小村落在历史的进程中所担负的喜与乐,爱与愁,进步与落后等农民问题。在作者近乎田野调查的描述中,农民的切实问题被形象地记录下来,从而也为读者刻画了一幅转型时期的现代农民生活的“清明上河图”。
精彩内容
磨盘洲吃过早饭,何袁氏就筹划着去磨盘洲拜菩萨。她考虑到自己年事已高,去磨盘洲的路程并不算太近,因此就希望能尽量轻装前行。她知道拜菩萨用的香烛鞭炮磨盘洲可以现请,随身只需带足香火钱就行。正月元宵刚过,按理天气依然寒冷,早上的霜依然铺了一地,可平日里冷冷的太阳到今天却有些火热,刚刚到树梢就把还贴着着红彤彤的春联的村子晒得暖和,村子里留下的几个老人已经争先恐后地把被褥抱出来晒了。她还没走到村口就感到身子在冒热气,考虑到要不了几个时辰就可以回转,于是又返回家中脱下了儿子媳妇买的她本来就嫌笨的羽绒服,同时落下了媳妇留给她她却觉得用不着的手机。她就这样轻轻松松地上了路。何袁氏走在去磨盘洲的路上。从她的村庄杨家岭到磨盘洲有七八里,一个来回也就十五六里,如果换作比现在年轻几岁,她并不需要太多时间。现在虽然已经八十岁了,可她耳不聋眼不花,腰板称得上硬朗,腿脚也还灵便,虽然体力不比当年,可包括往返加上在磨盘洲敬香逗留花上三四个小时也绰绰有余。中午饭食,只要口袋里装上一点还来不及吃完的年货就足可以对付。太阳朗照,天地间宛如编织着万千金线,金黄的油菜花在路两边绽放,满目的金黄让走在拜菩萨路上的何袁氏有一种居身光明广大、菩萨塑金的庙宇之中的错觉。许久没有亲近和打量的田园景色如此怡人,何袁氏的心情不免愉悦了起来。从杨家岭到磨盘洲,要过几个村庄,走一座桥,上下几个小坡,要穿过一大片旷野,直到远远看得见村庄……这段路,何袁氏走了三十多年,她当然是再熟悉不过。三十多年前,她遭遇了一场天大的变故。她的丈夫,一个看起来身体壮得像牛的庄稼汉,顿顿吃得下三碗干饭的中年男子,突然病亡,丢下四个大大小小的孩子给她。命运给她开了一个残酷的玩笑,让她这个无辜的人,承受了最为严酷的刑罚。她感到天都塌了。死去丈夫的可怖面容,镜中自己急剧消瘦不成人形的样子,孩子们因父亡而变得病态的、隐忍的、可怜巴巴的眼神,都让她产生一种命运里有恶鬼随行的错觉。她当然义无反顾地挑起生活的重担,把汗水摔在地上,指望几亩薄田能淘出金子,一块硬币恨不得掰成两半,自己身材再瘦小,两手一无所持也要挣扎着把孩子们抚养成人。可是,她需要命运给她一个说法,她到底有何错,为什么把这么重的惩罚给她。她需要天地间有一个依靠,一个信念,在她每次快扛不住的时候能支撑她继续。她更需要一个保护神,保佑她的生活再也不要出什么纰漏,保佑她的孩子们平平安安没病没灾地长大。这个可怜的人把日子过得风声鹤唳、草木皆兵,已经到了一根稻草都可以压死她的地步。她的孩子一有头疼脑热,她就茶饭不思、夜不成寐,窗外一声乌鸦的聒噪,饭桌上一只饭碗的失手打碎都会让她疑神疑鬼,一颗偶尔出轨的火苗,都让她怀疑是一场火灾的索引。她多需要有谁能给她搭把手!在村里同样苦命人的引导下,她开始走向了磨盘洲。村里同样苦命的人说磨盘洲的菩萨最灵验,并且对乡下人最为慈悲。村里人举例说谁谁谁向磨盘洲的菩萨求子得子,谁谁谁久病不愈,向磨盘洲的菩萨祷告结果不出一周竟奇迹般痊愈,谁谁谁家的牛不见了也向菩萨问询结果牛自行回了家,谁谁谁长期到磨盘洲拜菩萨全家没病没灾,儿孙出入平安,老人颐养天年。在某年春节过后,何袁氏跟着村里的苦命人,第一次来到了磨盘洲,站在了被传得神乎其神的、一言不发的菩萨面前。何袁氏记得她第一次到磨盘洲的情景。在菩萨面前,她有些慌,好像她是一个做错事眼神躲闪的孩子,而菩萨就是威严地盯着她看的爹和娘。因为是头一次来,她还不能做到从容,头也是磕得潦草不堪。她在心里把自己的苦楚向菩萨说了一遍,因为苦楚太多,她在蒲团上待的时间就有些长,让村里与她同来的人颇有些不耐烦。她还斗胆在心里询问了菩萨,为什么让她遭遇那么多的苦,给她这个从未作恶的女人施以如此重的惩罚。她当然也向菩萨求了福,祈望菩萨能保佑她的生活不要再出什么差错,儿女们能平安健康长大。她祈愿她那死鬼丈夫的死抵消掉她家命运里该有的不幸,如果这个家还有她所不知道的孽债未还,如果还要有报应,就请全部应在她的身上。到了最后,她担心菩萨没听清楚她说的,就在心里把所有的话复述了一遍。也许是她的苦过于沉重,也许是她担心菩萨因为她的祈求太多无法全部满足,她发现自己泪流满面,直至失控哭出了声。从磨盘洲回来后,何袁氏隐约感觉到菩萨应了她的祈愿,成了她的家庭中隐形的成员。一些细微的征兆可以证明这一点:她的失眠变好了。她的头发不再大把大把脱落了。她的只有两三岁的儿子让她揪心的咳嗽自行止住了。她家的牛怀上了小牛崽她也认为是菩萨的功劳。她种的一棵南瓜苗少有地结下了十多个硕大的南瓜,她也认为是菩萨暗中施了援手。因为自觉与菩萨搭上了关系,她的心不再是整天空落落的,而是没来由的有了安慰。有一天她从镜中看到,她的那张曾经在突如其来的厄运中如纸惨白的脸又恢复了些许红润,嘴角不由得绽开了笑意。从此每一年春节过后,她都要去磨盘洲拜菩萨。每年观音菩萨六月或九月的生日(传说观音菩萨有三个生日),如果她有闲暇,也会去磨盘洲拜一拜。她有时和村里同样苦命的人去磨盘洲,有时候她会孤身一人去磨盘洲,为的是能让菩萨见证她的诚心,能更清楚地听到她的苦辛和祈愿。每次去磨盘洲,她会首先还上前一次许下的愿,感激菩萨应了她的请求,然后重新许上一个新的愿。由于经常去拜菩萨,她已不再是初次时的潦草和慌张,而是从容,笃定,庄重。她把香插得整齐,比往自己头上夹上发夹还要认真,头也磕得端庄有序。每一次跪拜,都可以看出她要低到尘埃里的决心,每一次双手合十的祷告,她的眉宇间都充溢着把自己完全托付给菩萨的虔诚。几十年来,何袁氏感觉自己从菩萨那里得到了太多的好处。她的孩子们缺衣少食却个个长大成人。他们并没有因为父亲的缺席就心虚气短缺精少神。她的三个女儿都先后成了妻子、母亲。她的女婿都是本分人。她们的孩子个个都聪明伶俐。她最小的幺子福米早在十多年前就跟着村里的年轻后生去了广东打工,成了广东许多公司争抢的高级模具师。他也早在十多年前结婚生子。她这个苦命的寡妇,先后成了外婆、奶奶,成了由她衍生的大家庭的头面人物。那是一个祥和的大家庭,这个大家庭里的所有人,都富足有余,平安有余,积善有余,身体康健有余。村里当年一起与她去磨盘洲拜菩萨的苦命人经常笑说她是一根苦藤上结了甜瓜。想想三十多年前的疾苦,看看今天儿孙满堂的好日子,何袁氏有理由认为那都是菩萨给她的馈赠。何袁氏应该对磨盘洲的菩萨感恩戴德。何袁氏应该经常去磨盘洲走一走,多向菩萨嘘寒问暖,像任何一个知恩图报的人那样。可是何袁氏已经有三五年没有去过磨盘洲了。何袁氏感到自己对磨盘洲的菩萨亏欠得太多了。她的心里常常涌起天大的不安。今年春节刚过,她根本不听媳妇和孙子要她一起进城的苦口婆心的劝告,独自一个人留在了家中。趁着这难得的艳阳天,她从家中走出,不紧不慢地走在了通往磨盘洲的路上。空气中的油菜花香让人迷醉。路边的水渠中流水潺潺,十分悦耳。鸟的叫声让人疑心春天已临。走了七八里的何袁氏也没觉得太累。她来到了磨盘洲,心满意足地又跪在了菩萨的面前。她虽然已经是一个八十岁的老妪,可是在菩萨面前,她感觉自己依然是一个爹娘怀中需要呵护的孩子。她燃香,磕头,煞有介事地在心里向菩萨和盘托出她的念想。她首先当然要感激菩萨这么多年来对她这个苦命人的支撑、护佑,是菩萨的援手让她有了相对安稳的今天。她依然祈求菩萨能继续保佑她一家老小命里风调雨顺,脚下出入平安。她祈望菩萨能给她的已成家庭主妇的三个女儿的命里再加点蜜,让长期在广东打工谋生的儿子福米多一点好运少一点风雨,她那十来岁的孙子还要多有三分聪明,她与一起陪读的儿媳瑞英能多一点相互理解和宽容就更好。因为想到自己可能要得太多,有一会儿她的脸变得红了起来。然后她祈求菩萨的谅解,因为自己年事已高,到了风烛残年的地步。她的生活这几年也发生了不大不小的变化:形势逼迫,乡村教育不成样子,她只好离开了村庄,与儿媳一起去了几十里外的县城,做了孙子的陪读。她已经再无时间和精力年年来磨盘洲拜菩萨。以后的她,只能把菩萨装在心里,只在每月初一、十五,燃香向着磨盘洲的方向遥祝祷告。及至末尾,她看看时间还充足,还和菩萨说了好一阵子的话,比如乡下没人种地,村庄没人留守,村子里空荡荡呀,早上鸡叫听起来都有几分瘆人,菩萨怎么不管管,等等等等。她想这话说给儿媳听儿媳会嫌她啰唆,但在慈悲为怀的菩萨面前,一切都无须遮掩,即使她说错了菩萨也是会原谅的呀。何袁氏肚子有些饿了。她向守庙的人讨了一碗水。和着水吃完了她带到路上的年货,她慢慢起身走出了磨盘洲。一路上她都不停地向着磨盘洲回望,直到磨盘洲在视线中变小、消失,才心满意足地往家的路上走。拜过了菩萨之后,她的心情是愉悦的,有一种如释重负的轻松与坦然。她想她的心愿已了,明天她该乘车去县城,一心一意与儿媳一起在某间简陋的出租房里做孙子的陪读。在孙子的诵读声中终老,其实也会是一件不错的事儿呢。此刻在空无一人的路上,油菜花香在空气中飘荡,鸟的叫声里没有丝毫不祥。她不知不觉来到了一条水渠前。那是一条其实不宽也不深的水渠,多少年来她往返磨盘洲能轻松迈过自不在话下。她满以为这一次也一样不会挡着她,结果她的运气并不是太好。她掉下去了。水渠两边的土块纷纷坠落。2吃过早饭,瑞英把照料孩子读书的事托付给了熟人,就急着与丈夫福米以及相关人等一起去磨盘洲拜菩萨。种种迹象可以表明这是非同寻常的一次出行:人人知道瑞英是个节俭成性的女人,在县城再远的路她都舍不得花钱坐车,上菜市场她总是与菜贩子将价钱讲了又讲,可是这一回她竟舍得花上三四百元一天的巨资租车去磨盘洲,并且到今天为止已经租了三天了。车上坐着的人福米三个姐姐家皆有代表,福米也千里迢迢从广东赶回,这只有过年过节娶亲嫁女才有的阵势,在不年不节的今天竟然发生了;车厢里几乎所有人的脸上都忧心忡忡,虽然有人间或地起些貌似轻松的话头,也有人故意附和着说些不咸不淡的话,其实不过是改善车厢里压抑得人人想跳车的气氛。他们何以如此兴师动众不计成本忧心忡忡?熟悉他们的人知道,他们摊上大事了。他们的母亲、婆婆、岳母,那个叫何袁氏的八十岁的老太婆,在几天前突然与他们失去了联系,至今下落不明。这件事的前因后果瑞英祥林嫂般说了多次,大家早已耳熟能详。元宵刚过,到了儿子寒假结束学校开学的时候,老太婆本应同往年一样随她一起坐车到县城做她孙子的陪读,一家老小在一起也方便相互照料。可老太婆临期说自己要在乡下多住几天,理由是她要腾出时间去磨盘洲拜菩萨,给出远门的儿子、读书的孙子祈福。老婆子身体尚好,腿脚还利索,耳不聋眼不花,神清气爽,生活自理毫无问题,也没有什么会骤然发作的暗疾让人担心。磨盘洲也不算远,她去磨盘洲也是熟门熟路,平日里听她说起磨盘洲都要听起茧来,瑞英觉得她独自一人在村里待上几天和去磨盘洲拜菩萨应该是一件可以放心的事。为以防万一,她给她留了一个手机。开头几天每天早晚两次和她通话都很正常,可是四天前瑞英反复拨打手机都无人接听,瑞英感到头一下子变大了。她匆匆从县城坐班车赶回家发现手机落在了家中,上面数十个未接电话都是她拨打的,同样留在家中的还有老太婆可能嫌热脱下来的羽绒衣裤。她赶紧打电话给十多天前才去了广东打工的丈夫,三天来她与赶回家的丈夫租车跑遍了磨盘洲方圆数公里的地方,可是他们没有得到老太婆的任何消息。他们带着放大了的老太婆的照片,找遍了磨盘洲方圆数里的所有村庄,询问了留在那里的人们。他们给那些村庄里的陌生人或者熟人留下电话,请他们一旦有什么线索就立即告知,如果线索有价值他们一定酬谢。可是春节过后村庄能留下来的人已经少得可怜,除了少量因为有事还没来得及离开村子的中年男女,剩下的就都是神情呆滞、耳背眼花、弯腰驼背的老人。那些年轻的人们都已经坐着火车、汽车去了大城市打工,那些孩子们大多数都到了县城读书,许多老人和妇女做了他们的陪护,就像瑞英和福米一家那样。过去人声鼎沸、人口密度大得惊人的磨盘洲区域现在几乎成了废墟。他们因此并没有得到多少有价值的信息。他们在每个村庄的池塘、坟堆、井台、颓圮的老房子、荒废了的礼堂甚至臭哄哄的茅坑里搜寻,就连大量空置的乡村学校也没有放过,可是没有找到关于老太婆的蛛丝马迹。他们搜遍了磨盘洲方圆数里的每一个可疑的草丛、土堆、树荫处,甚至差不多把每块油菜花地都翻了一遍,可是连老太婆的影子都没见着。这种漫无目的的寻找让他们快要虚脱了。他们已经有了不祥之感。可是他们依然没有放弃。他们认为没有找到老太婆,老太婆平安的希望就一直存在。他们幻想着老太婆是不小心迷路了,磨盘洲处于一块有着数个平方公里的旷野中央,也是两个县的交界处,她往来磨盘洲正是太阳朗照时候,她不慎走岔迷路也是可能的事。说不定她正被本县或邻县的好心人家收留,媳妇和儿子电话她并没有记住,她用方言土语介绍自己别人可能无法弄清,只能等着他们找上门去。或许因为太阳热烈,正患感冒发烧的老太婆路上不慎晕倒,正好有好心人路过将她送到附近某座乡村诊所之中,尚没有进入他们的搜寻视野。等不久他们找到她的时候,世界会还给他们一个脸色红润的康健的母亲。或许正好在路上,他们的母亲突发老年痴呆症,或者遭遇了传说中的鬼打墙被路上厉鬼窃了魂,眼前风景来时道路自己是谁她已经全然忘记,只能一个人懵里懵懂信马由缰地走,即是如此也不至于这几天就会糟糕到极致,往来间只要有人迹就会赏她一口吃喝,这个世界肯定还没坏到见死不救的程度。他们这么想着,沉重的脚上就又有了几分力气,就连慌乱跳动的心也显得平稳了一些。他们的母亲生死不明,一切都悬而未决。他们在情急之下想到了要去磨盘洲拜菩萨。他们尚年轻,又自诩是这个社会里的新人,还没有到需要拜菩萨的程度,但这件事让他们有了信菩萨的愿望,因为下落不明的母亲信菩萨,并且在走失之前到过磨盘洲拜菩萨是确凿无疑的事。他们相信母亲的失踪与菩萨有了瓜葛,说不定母亲就是菩萨故意藏起来的,目的是要他们反省自己对母亲的孝顺程度,并且引领着年轻的他们来信菩萨。以前屡屡听母亲说起,磨盘洲的菩萨是他们一家的保护神,他们遇到了难题,自然想到向磨盘洲的菩萨来问计。他们来到了磨盘洲,跪在了菩萨面前。母亲的失踪让他们把头低到尘埃里。他们感恩菩萨这么多年对他们一家的护佑,表示他们其实在心里早就认下了菩萨的恩泽。然后他们开始了忏悔。他们悔恨自己在往昔曾经对母亲有过怠慢,比如打工的儿子每年都很少因为陪伴母亲留在家中多些时日,为了生计疏忽了对母亲的关怀,并不知晓母亲内心是否孤单,做儿媳的与她相处还没有到母女般的亲热程度,已经几年没有买过一件喜庆的衣衫给她。那些做女儿女婿的至今不知母亲的生日和喜好,过起年节每次都是塞些钱财了事。此次母亲失踪,肯定是菩萨的良苦用心,他们已是心领神会。他们一旦找到母亲一定视母亲如神灵,把母亲当作菩萨精心供养。他们渴望菩萨给他们一点儿暗示,为他们寻找母亲指一条明路。他们定当感谢菩萨的大恩大德,从此拜倒在他的面前,跟随母亲做他永远的信徒。拜别菩萨,他们又踏上了寻找母亲的路程。他们边搜索边商量着如果今天还没有消息,明天将扩大搜索范围,并且在本县与邻县两县电视台做寻人广告,沿途的村庄的电线杆上都要贴上有母亲相貌的寻人启事。可不多久他们接到了一个电话。电话里的人自称是磨盘洲某个村庄的捕蛇人。他说他在某条水渠里看到了一个老太婆,不知道是不是他们要找的母亲。他们没有想到磨盘洲的菩萨这么快就显了灵。他们驱赶着面包车没命一样地赶往捕蛇人所说的、他们没有来得及搜寻到的水渠,远远地看到了茅草丛里的母亲—— 她低着头,脸盖在土中。头上被风吹起的白发与茅草混迹。她的后脚还搭在水渠的这一头,前脚落在了水渠的下面。这相隔不宽的水渠,仿佛是故意设置在她面前的专为拘押她的用心险恶的刑具:她既不能抽回前脚退回到水渠的这一头,也不能收回后脚让自己落入其实并不深的水渠之中,然后找到低洼处爬到对面。她太老了,完全没有力气挣脱这一枷锁。或许她的脚摔折了,动弹不得,巨大的疼痛,让她挣扎一下都要晕过去。要让她化险为夷的可能性只有一种:有人正好经过施以援手——那其实并不需要花多少力气。她肯定喊过救命。肯定在心里祈求过菩萨。可是这曾经人声鼎沸的乡村,现在没有人。他们都到城里打工去了。他们都到城里陪孩子读书去了。她所有的喊叫,找不到一双能接纳的耳朵。这数平方公里的旷野,宛如坟场一样死寂。手机这唯一的救命稻草被她留在了家里。天黑下来了。脱掉了衣服的她肯定又冷又饿。她在这饥寒交迫叫天不应叫地不灵的状态下坚持了多久?然后她绝望了,把脸埋在了土里,渴望从这土层里吸收到一点温暖,又是唯恐田鼠或其他兽类趁她临终后毁了她的容。他们一起号叫着“妈妈”,齐齐对着她跪了下去。他们把头低在尘埃里。他们尖锐的哭声,在这大地深处传开,并且渐远。
相关推荐
— 没有更多了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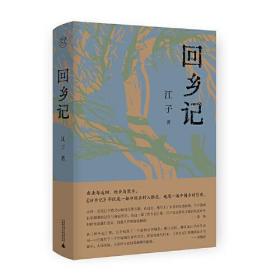







以下为对购买帮助不大的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