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布达佩斯大饭店
正版图书,可开发票,请放心购买。
¥ 155.24 7.8折 ¥ 198 全新
库存7件
广东广州
认证卖家担保交易快速发货售后保障
作者马特·佐勒·塞茨
出版社九州出版社
ISBN9787510892844
出版时间2021-05
装帧精装
开本其他
定价198元
货号31185721
上书时间2023-09-02
- 店主推荐
- 最新上架
商品详情
- 品相描述:全新
- 商品描述
-
作者简介
编著者简介马特·佐勒·塞茨(MattZollerSeitz)是RogerEbert影评网的主编,《纽约》杂志的电视节目评论家,以及荣登《纽约时报》畅销书榜的TheWesAndersonCollection的作者。他也是TheHouseNextDoor博客的创始人和原编辑,PressPlay视频博客的联合创始人以及艾伯拉姆斯出版社2015年秋季出版的TheOliverStoneExperience一书的作者。
插画家简介马克斯·道尔顿(MaxDalton)是一位居住在阿根廷布宜诺斯艾利斯,并时常前往巴塞罗那、纽约和巴黎旅行的绘画艺术家。他自己出版了一系列书籍,也为其他书籍绘制插画,其中就包括了艾伯拉姆斯出版社2013年出版的TheWesAndersonCollection。马克斯1977年开始学习绘画,2008年起为音乐、电影和流行文化产业制作海报,很快便成为行业中首屈一指的名家。
译者简介邹艾旸,策展人,写作者,西班牙IESE商学院工商管理硕士,策展实践方向主要为短片、早期电影、实验影像、女性研究和跨媒介艺术项目。
目录
引言
作者序
影评
第一幕 欧洲的概念
第一次对谈
恰如其分的探索:专访拉尔夫·费因斯
穿着即人:《布达佩斯大饭店》与电影服装的艺术
韦斯·安德森风尚:专访米莱娜·卡尼奥内罗
第二幕 微缩景观
第二次对谈
《布达佩斯大饭店》的音乐:地点、人物与故事
私密之声:专访亚历山大·德普拉
宏伟的舞台:《布达佩斯大饭店》的美术设计
保持运行:专访亚当·斯托克豪森
第三幕 在阿尔冈昆酒店
第三次对谈
昨日的世界
斯蒂芬·茨威格作品摘选
迥异的元素:专访罗伯特·约曼
韦斯·安德森的4∶3画幅挑战
十字笔杆同盟
作者简介&致谢
作品索引
图片版权说明
内容摘要
本书是获奥斯卡4项大奖的影片《布达佩斯大饭店》唯壹官方全纪录。这部由韦斯·安德森执导的超人气作品,凭借独特的叙事、迷人的视觉风格和对画面的偏执追求而为人津津乐道。全书由他亲自授权、把关设计,以精彩图文完美还原了“大饭店”的诞生始末,揭秘了这位天才独壹无二的招牌美学。
这里不仅有足量一手访谈、深度评论、彩蛋花絮,更收录了逾600张独家美图,含导演亲绘分镜、未公开设计稿和超萌专属插画……定格了影像中值得反复回味的细节,给观众以放大镜方式重新体验的机会,让人身临其境、宛如站在拍摄现场。
精彩内容
正文赏读昨日的世界文/阿里·阿里康斯蒂芬·茨威格生活的世界和那个他哀悼其消逝的世界是两个截然不同的实体。也许可以称前者为“现实”,后者为“幻象”,但我们不应该如此武断。在这里,当讲故事成为主题,现实与幻象之间的界线便不那么清晰了。要明白这种现象产生的原因,我们不妨想一想以下两幅人像。
第一幅是茨威格最广为人知的头像照片,被印在他作品无数版本的封页上。他的头部呈45°朝向镜头,食指放在脸颊上,向后世读者投出一个谜样的微笑。他似乎既调皮又忧郁。而精心修剪的胡须、浆得笔挺的衣领、饰有纹理的领带和附缀金属夹、紧贴头颅的油亮发丝,也让他颇似一位时髦讲究的公子。
第二幅是一张与《布达佩斯大饭店》的电影预告片同时放出的宣传剧照:拉尔夫·费因斯饰演的大饭店礼宾员古斯塔夫先生的照片。费因斯的扮相与茨威格非常相似。一开始,我以为这只是个令人愉快的巧合,看完电影后才意识到并非如此。它交织着风趣机智和忧伤怀旧的情绪,对“失去”的概念无比执着,从头到尾笼罩着茨威格式的柔光。韦斯·安德森在《布达佩斯大饭店》开头就承认了这一点[“茨威格式(Zweigesque)”这个词并非我的创造,而是他的]。姓名不详的祖布罗卡阅读爱好者拜访了国宝级文豪的墓地,他的铜像上刻着简单的名号“作家”,铜像神似茨威格晚年的形象。1985年段落中,亲自登场的作家造型与茨威格有着细微的相似之处,而青年作家(字幕称为“年轻作者”)和古斯塔夫先生也是如此。“看到相似之处了吗?”古斯塔夫一边问泽罗,一边模仿着《拿苹果的男孩》画中人物的动作。而且,好像怕接下来的故事仍未证明对茨威格的绝对拥护,安德森特意在片尾字幕中再次写道:“灵感来自斯蒂芬·茨威格作品。”安德森甚至不满足于仅仅这样致敬,还和普希金出版社(PushkinPress)合作策划了一部茨威格作品选集,前言由自己和另一位编剧雨果·吉尼斯撰写。
你可能会想:一个是20世纪末维也纳风度翩翩的作家,作品无论多受推崇,却仍无法渗透进大众文化;另一个是来自得克萨斯州的当代电影人,新片在前者去世72年后上映,他怎么会对这位作家产生了亲切感呢?
这个问题的答案或许可以在奥地利与斯蒂芬·茨威格紧密结合的历史之中找到。
数世纪以来,维也纳始终捍卫着欧洲的理想,抵御东方的侵袭。这座城市坐落于阿尔卑斯山东陲,是相对容易攻克的欧洲平原和来犯的撒拉森人(Saracen)之间仅有的屏障。在维也纳,古罗马人曾筑起防御工事,抵抗来自东部的日耳曼部落,这座城市也阻挡了1529年和1683年奥斯曼异教徒的两次侵略。
待土耳其方面的威胁退却,启蒙时代伊始,维也纳终于获得了喘息与反思之机。1804年,拿破仑战争期间,维也纳成为奥地利帝国的首都。63年后,随着1867年奥地利-匈牙利折中方案的实行,它又成为重新统合的哈布斯堡帝国首都和新诞生的奥匈帝国首都,像灯塔一般吸引着八方才俊。
新移民纷纷到来,宏伟的环城大道(又名“戒指路”)建成,昔日郊区并入城市,维也纳的人口也从1870年的90万增长到1910年的200余万。城市散发出蓬勃朝气,无限的可能性让奥匈帝国的子民从各地涌入首都。然而,这个由15个民族构成的庞大帝国中,仅有奥地利和匈牙利享有民族国家地位,因此出现了“V?lkerkerker”一词,意即“聚集民族的监牢”。
但在茨威格生活的城市里,情况却并非如此。矛盾始终存在,但动乱却鲜少出现在城市中。风平浪静的维也纳仿佛拥有某种与生俱来的能力,可以从多民族混乱中营造一方和谐的国际化天地。18世纪后期的数十年间,自由主义、世俗主义、资本主义、城市化、民族主义和社会主义是城市中占据支配地位的力量,尽管有时彼此冲撞,却共同发展。它们使从前备受污名化的群体——特别是犹太人——在经历数世纪的排斥后,重新获得了成功。
咖啡馆是维也纳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面向所有人开放的场所。人们聚集在传统的大理石桌面周围,互相交谈、打牌、阅读报刊和书籍。茨威格认为,维也纳的国际化气质很大程度上可以归功于咖啡馆带来的每日国际快讯和文化评论。在某个时期,希特勒、托洛茨基、铁托、弗洛伊德、斯大林都在同一个街区活动,甚至可能在同一家咖啡馆流连过。在这座梦之城工作的西格蒙德·弗洛伊德让解析梦境成了一门科学。近乎情色的新艺术运动(Jugendstil)的曲线,柔和地蜿蜒在古斯塔夫·克里姆特的画作中,在古斯塔夫·马勒(GustavMahler)和胡戈·沃尔夫(HugoWolf)的复调音乐中,在奥托·瓦格纳(OttoWagner)的建筑中。文学方面,阿图尔·施尼茨勒(ArthurSchnitzler)、赫尔曼·巴尔(HermannBahr)、彼得·艾腾贝格(PeterAltenberg)写就了形式创新的散文、小说和专著。新艺术运动很快便遭遇独辟蹊径的表现主义风潮的挑战。打破陈规者层出不穷,在音乐领域是阿诺德·勋伯格(ArnoldSch?nberg)和阿尔班·贝尔格(AlbanBerg),美术领域是奥斯卡·柯克西卡(OskarKokoschka)和埃贡·席勒(EgonSchiele),建筑领域是阿道夫·路斯(AdolfLoos),文学领域是博学的卡尔·克劳斯(KarlKraus),哲学领域
则出现了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LudwigWittgenstein)。
然而,单纯认为世纪末的维也纳充斥着胜利昂扬和面向未来的坚定信念无疑十分天真。大多数时候,维也纳知识分子们都欢欣鼓舞,但他们同样为这个世界能否存续而深感忧虑,因为代表无理性和残暴统治的势力始终在后台蠢蠢欲动,等待着登台的时机。
维也纳19世纪后期的变革阶段,茨威格的人生画卷徐徐展开。1881年,他在这座城市出生,父亲是富有的纺织实业家,母亲则是犹太裔意大利银行豪门千金。财富成为他们进入维也纳社交界的门票,而他们一边庆幸于免遭部分公然反犹行径的影响,一边仍不可避免地惴惴不安。茨威格一家知道,他们永远无法成为奥地利贵族士绅阶层的一员。用当时的话来说,他们“明白自己的斤两”,这也是非犹太精英团体接纳他们的原因。
一些其他犹太作家质疑这种接纳本身带有讽刺意味,但茨威格没有。他显然意识到了这一点,但并未过多纠结。“我们得以将私生活塑造得更加个性化,”他写道,“我们生活得更富国际化,全世界都向我们开放。”年轻时生活在19世纪晚期维也纳的经历,更加坚定了茨威格的自豪感。“在欧洲,几乎没有一座城市像维也纳这样热衷于文化理想。”他写道。到了世纪之交,人们对于艺术有了全新的理解。“我们青年时代真正伟大的经验,在于意识到艺术方面有新事物即将出现,它们比我们的父辈和周围的人曾满足过的那些更为热烈、更加艰涩、更富有诱惑力。”此情此景令年轻的维也纳人无比沉醉,以至于他们根本没有意识到这些“美学领域里的转变只不过是许多更深远变化的先兆。这些变化将动摇和最终毁灭我们父辈们的太平世界”。
尽管心怀爱国热情,茨威格仍拒绝在一战烽烟燃起时拿起枪上前线。他在战争委员会的档案室工作,成为一名反战主义者和欧洲一体化的倡议者。当他的非暴力倡议引起当局警觉时,他搬离了维也纳,首先前往苏黎世,战后短暂居住在柏林。他最终定居在奥地利萨尔茨堡附近的卡普齐纳山上一座别墅里。他的山间别墅成了欧洲文人墨客心中的文化朝圣地,仿佛一座“花花公子庄园”中的阿尔冈昆圆桌,欧洲高雅文化圈的三教九流都云集于此。“罗曼·罗兰曾在我们那里住过,”他写道,“托马斯·曼也是。我们曾在家中友好地接待过H.G.威尔斯(H.G.Wells)、霍夫曼斯塔尔(HugovonHofmannsthal)、雅各布·瓦塞尔曼(JakobWassermann)、房龙(VanLoon)、詹姆斯·乔伊斯、埃米尔·路德维希(EmilLudwig)、弗朗茨·韦尔弗(FranzWerfel)、格奥尔格·勃兰兑斯(GeorgBrandes)、保罗·瓦莱里(PaulValéry)、简·亚当斯(JaneAddams)、沙洛姆·阿施(ShalomAsch)和阿图尔·施尼茨勒。在音乐家中,我们接待过拉威尔(Ravel)、理查德·施特劳斯(RichardStrauss)、阿尔班·贝尔格、布鲁诺·瓦尔特(BrunoWalter)、巴尔托克(Bartók),此外,宾客中还有来自世界各地的画家、演员和学者。”茨威格走上别墅的露台,便能隔着国界线远眺德国南部。“我们在那里和所有宾客一起度过漫长美好的时光,坐在露台上眺望美丽静谧的景色,怎么也想不到,就在正对面的贝希特斯加登山上住着一个将要毁坏这一切的人。”《昨日的世界》中这样描述。他的阿尔卑斯山间别墅代表着希特勒处心积虑想要消灭的一切,并不仅仅因为土地所有者是犹太人,世界主义、平等主义、欧洲社会主义的思想才是纳粹真正想践踏的对象。
一战让国界线变得清晰起来。茨威格痛恨这种“现代潮流”。他将护照的发明视为这病症的载体。“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最为生动地证明世界巨大倒退趋势的行为,莫过于限制人的行动自由和公民权利,”他满怀痛苦地写道,“1914年以前,世界属于全人类。每个人想去哪里就去哪里,想在那里待多久就待多久……没有许可证,没有签证,更不用说刻意刁难。如今的国境线在所有人对他人病态的不信任之中变为纠缠不清的繁文缛节,而从前它们不过是地图上象征性的划线而已,可以像越过格林尼治子午线一样无忧无虑地越过那些边界线。”茨威格相信,民族主义在一战之后才出现并撼动了世界。这种精神瘟疫酝酿出的最初症状是仇外:对外国人的病态厌恶。“曾经只用来对付罪犯的一切侮辱手段,现在都施加在每一个在旅行前或旅行中的普通人身上。”1934年,随着希特勒在德国当权,茨威格离开了奥地利。他首先搬去伦敦和英格兰约克郡,之后前往纽约,最终定居在巴西彼得罗波利斯。他始终热爱旅行,仿佛患上了一种只能用德语“fernweh”(直译:对远方的渴慕)一词来描述的疾病。但在英格兰和纽约时,他写过自己痛恨那种“被视为‘外国人’的不快感受”。他确信身处异国他乡之人将逐渐失去自尊:“我可以毫不犹豫地承认,从不得不靠在我看来十分陌生的身份文书或者护照生活的时候起,我再也感觉不到自己完全属于自己。我自主身份中的某一部分随着我原本的、真实的自我一起永远被毁灭了。”历史让年轻的茨威格多产而自信,对未来充满信心,但也是历史猝不及防掉头从他身上碾过,夺走了他的理想主义和玫瑰色幻梦,空余苦甜交织的安慰奖—记忆,在他的重述中愈发美得不切实际。他的不少关于青年时期维也纳的文章是在生命尽头,也就是20世纪30年代末,法西斯的幽灵盘旋于欧洲上空之际写就的。支撑他生命的是从记忆里世界的混沌中提取的短文和风景画,但他也始终明白自己“将文化设想为一种精神的玻璃弹珠游戏”只是多愁善感罢了。他对不复存在已久的维也纳的眷念是那样虚幻而摇曳,正如他在《昨日的世界》中坦承的:“在巨大的风暴早已将一切击得粉碎的今天,我们终于明白曾经的太平世界不过是一座空中楼阁罢了。”诚然,茨威格的记忆很主观,但围绕的核心依然是真实。某些闪烁着荣耀与美好的事物的确在一战中摇摇欲坠,而在二战中则被摧毁殆尽。纳粹统治的余波中,世纪之交的富裕表象大都烟消云散,孕育这繁荣的文化土壤也不曾幸免于难。茨威格在第二任妻子的陪伴下选择自杀是在1942年此时他已为欧洲及其文化的未来绝望了多年。茨威格所颂扬的过往是欧洲高雅文化和人性良善行将消亡的余晖,是一种永远丧失的纯粹。
不过,也并非永远:茨威格青年时代的维也纳在《昨日的世界》里重获新生。它同样存活在小说和故事的章节中,这些作品重述诗人、哲学家、文艺爱好者及其拥趸之间的智力竞赛和惺惺相惜,追忆着叙述者许久前就已离开之处曾经的光彩。
茨威格笔下,讲故事的人都可信吗?连他们自己都在怀疑。他的作品中满是这样的情形:角色挣扎着想记起事情,或不确定自己是否记错事情,或需要花时间从潜意识之中挖掘细节。我们经常发现自己看到的并非事件原貌,而是一种私人的、抒情的重现——一种蕴含着等同于乃至某种意义上超越事实的情感的记录。讲述方式大于故事本身,讲述者体验到的情感更大于讲述方式,而读者心中涌起的情感则最为重要。
《布达佩斯大饭店》清楚地明白这一层叠效应,并将其嵌入情节之中。故事的第一层中,年轻的泽罗·穆斯塔法从古斯塔夫先生那里学到了人生、爱与酒店管理的经验。大饭店的灿烂岁月是欧洲高雅文化的集中体现——电影中变换浓缩的版本正是《昨日的世界》里那个让作者醉心重述的奥地利。这是占据电影最大篇幅的一部分。古斯塔夫先生是一位充满魅力的花花公子,他人格化了茨威格眼中旧日欧洲的一切:鲜明的个人风格、世故的幽默感、极具感染力的乐天性格中闪现着智慧、欣赏传统的同时拒绝被传统束缚,他还有强大的适应力,让他得以逃离监狱疾走乡间,躲避着敌人的追踪,成功夺回《拿苹果的男孩》。
第二层故事发生在1968年的框架中,老年泽罗向青年作家饱含深情地回顾30多年前的往事,或者正如茨威格的某部短篇小说的标题那样,是“一个在黄昏中讲述的故事”(AStoryToldInTwilight)。
第三层故事由老年作家讲述,他在1985年的段落中向观众“展示”了前面的两层故事。古斯塔夫和青年泽罗的冒险被放置在数十年前另一个老人对故事的陈述之中,而数十年后,这个故事由如今的老人再次讲起。
公墓戏则是电影的第四层:开头结尾两段公墓戏将整个故事框起来。一位年轻女子在约2014年阅读了作家的书,深受触动,甚至来墓前凭吊,想象出整个故事。
而电影还有第五层。如果能发现它,就能理解一位导演将他深爱的源于现实生活的真正艺术进行转化的机制,创作出一部以从未存在过的虚构欧洲为舞台的电影。
尽管茨威格所写的传记和专著中,确切直白的叙述屡见不鲜,但他的虚构作品却如同套娃:故事中装着故事,由多个叙述者讲述,发生在不同的时代和遥远的彼方。《布达佩斯大饭店》也利用了这种手法,由前文提及的一系列叙述者共同推动故事发展,并在此过程中将事件抽象为传奇。
电影并未限于自青年泽罗、老年泽罗、青年作家、老年作家,或公墓里虔诚的年轻女子中任何一个人的视角,而是所有人视角的融合。它同样也是安德森眼中的世界。电影最显著的优点在于谦逊。它是80年后,远隔重洋的一位美国导演对铸就他幻想的作家的致敬。能写出这样一部天马行空的电影,导演绝不可能不热爱茨威格。而他同时也很清楚自己是一个影像制造者——一个讲故事的人,词语只是他织就电影的一部分材料,情节的经纬延展在近似真实而非真实的另一个维度之中:在那里,纽约不是纽约,海洋不完全是海洋,印度也不是现实中的印度。正如片中充满对茨威格本人及其作品典故的致敬,却并非直接改编自他任何一部作品。
然而,在这样精心设计的间接致敬中,《布达佩斯大饭店》成功地捕捉到了一种茨威格式的特质。现在看来,这种特质似乎正源于激发茨威格创作灵感的失落情绪。他的虚构作品,尤其是回忆录,给人的感觉像在试图复活某种发生的瞬间便会死亡、只能存活在讲述者记忆之中的经历。电影里的作家唯恐这种经历若不落于纸面,便会永远消失。
借助层叠叙事的魔力,茨威格的文字与安德森的电影融合为一个故事,讲述了人们对故事的渴望。在1985年的“序章”中,作家对摄影机说话,回忆起他居住在与电影同名的山间大饭店里,从“文士热”中逐渐恢复的那个八月。那座行将就木的建筑几乎是一片废墟,仅仅招待着几位形单影只的客人。一天夜里,年轻的作家发现一位老人带着“不易察觉的忧伤”端坐在大堂他就是泽罗·穆斯塔法,酒店的拥有者,而他主动提出要为作家讲述“这片迷人的旧日废墟”的故事。
安德森在整个开场段落中把玩着画幅比例:1.37∶1、1.85∶1和2.35∶1,一种画幅对应一条时间线,收缩和扩展空间,以电影化的语言呈现出故事层层嵌套的本质。不断变化的长方形黑边将“框架策略”(framingdevice)具象化,同时为画面中出现的其他“框形物”—房间和电梯、窗户和门扉、油画和盒装甜点—赋予另一层重要寓意。当然,这种手法自身便是对茨威格作品的隐喻。在他的故事中出现了大量怀揣秘密、内心煎熬的角色,这些秘密也经常在事后被“框架”裱起,或者封存在日记和信件中,变成回忆。
层次之上堆叠层次,画框之中还有画框,故事之中套着故事,纷繁的技法丝毫没有削弱电影的情感核心,而是共同成就了这个关于故事的故事。茨威格既是老年作家,也是青年作家,是老年泽罗亦是少年泽罗。他们代表着高度风格化的欧洲气质,让恩斯特·刘别谦、比利·怀尔德、马克斯·奥菲尔斯等导演迷恋不已,安德森在缪斯茨威格之外也在片中对这些电影人进行了致敬。当然,正如布达佩斯大饭店的繁华在战争到来后遍布的暴行之下迅速颓败,古斯塔夫先生身上那属于旧世界的魅力也将被闷闷不乐的让先生取代,只看工资的让先生奔走在曾是一座殷勤好客的宫殿、现在却人迹罕至的废墟里。
茨威格的阿尔卑斯山间别墅和布达佩斯大饭店之间有着显而易见的相似性。两者的呼应体现在一连串的关联中:茨威格热烈颂扬欧洲消逝的过往,缅怀自己的从前;古斯塔夫先生则致力于提前杜绝失去的可能性,不让他挚爱的大饭店落入“肮脏、该死、满脸麻子的法西斯混蛋”手中或被炮弹炸成灰烬;老年泽罗让古斯塔夫先生的传奇在岁月流逝中存续;而作家则将故事传给了未来的世世代代,打断开场白后站在他身边的孙子就是他们的代表。这一系列拯救故事的行为由一只粉色的门德尔饼屋包装盒承载,头尾的公墓场景为它系上蝴蝶结。电影就是这本书,书是泽罗的故事,泽罗的故事是古斯塔夫的故事,古斯塔夫的故事是布达佩斯大饭店的故事,而布达佩斯大饭店的故事也是茨威格阿尔卑斯山间别墅的故事,是奥地利的故事,是欧洲的故事,是万事万物的故事。这一切都已经离去了,消失了,再也无法挽回。唯有故事永存。
相关推荐
— 没有更多了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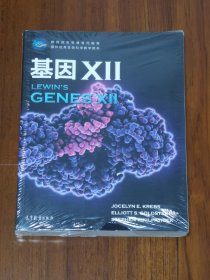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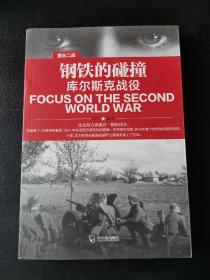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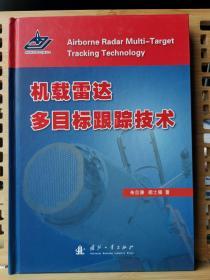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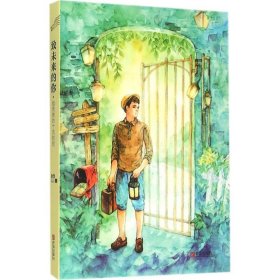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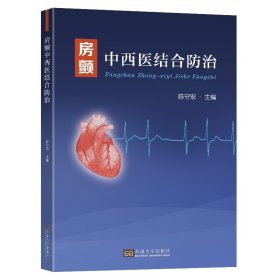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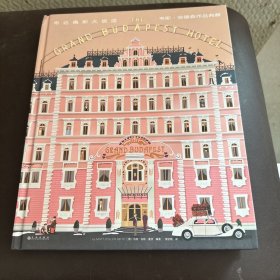






以下为对购买帮助不大的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