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古笔(精装)
一本书读懂毛笔的前世今生。
¥ 47 5.9折 ¥ 79 全新
仅1件
黑龙江哈尔滨
认证卖家担保交易快速发货售后保障
作者王学雷 著
出版社中华书局
ISBN9787101153149
出版时间2022-02
版次1
装帧精装
开本16开
纸张胶版纸
页数174页
字数370千字
定价79元
上书时间2024-09-14
- 最新上架
商品详情
- 品相描述:全新
- 商品描述
-
1.文献、文物、图像相结合,图文并茂,信而有征。
2.全书近200幅珍贵图片全彩印刷,细腻、生动。
3.作者具备田野考古背景,拥有丰富的书法创作经验,让毛笔史的书写言之有物。
内容简介
毛笔不仅是中国传统的书写工具,更是中国传统的一个重要文化符号。它在历史的演进中不断变化,成为各个历史时期文化风貌最重要的塑造者之一。
“蒙恬造笔”究竟可不可信?“兔毫”和“狼毫”出现于什么时候?古人更偏爱哪种动物毛制的笔?“汉居延笔”是怎样被发现的,后来又经历了怎样坎坷的迁徙之路?王羲之、王献之用的毛笔,和今天的毛笔有什么不同?今天的毛笔是“进化”还是“退化”了?汉唐时代笔管,其制作究竟有多奢丽?西方的“毛笔”与中国毛笔有哪些异同?字的好坏和毛笔的关系究竟有多大?存世的汉唐古笔文献中,还蕴藏着哪些古笔的信息?
本书通过大量史料和考古成果,呈现宋代以前毛笔的形态和发展,并由此探讨早期书法、绘画艺术发展及文化传播背后,工具所发挥的重要而又奇妙的作用,揭示毛笔的制作、传播、使用等方面有意思的文化现象。
作者简介
王学雷,江苏苏州人。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苏州市书法家协会理事、苏州市评论家协会理事、苏州大学艺术学院书法篆刻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员。现任苏州大学第二实验学校副校长。发表论文40余篇。著有《古笔考:汉唐古笔文物与文献》《〈砖塔铭〉与〈瘗琴铭〉:清人与碑帖的发现、临摹、翻刻及范本选择问题》《续补藏书纪事诗笺证》(即出)。论著曾获第五届中国书法兰亭奖理论奖、全国第八届书学讨论会三等奖。治学之余亦从事书法创作,作品多次在全国赛事中获奖展出。
目录
序一 张朋川
序二 薛龙春
绪言
上卷 汉唐古笔考
一、 “考古类型学”与早期毛笔制作形态
二、 “汉居延笔”的发现、图像与踪迹
三、 东晋束帛笔头考
四、 晋唐毛笔制作中的“缠纸法”
五、 蠡测“二王时代”的笔
六、 兔毫二题
七、 出土“狼毫”笔存疑
八、 汉唐时期的兔毫产地
九、 管杆小识
十、 “彤管”——古笔研究中一个被误解的名物
十一、 汉唐时代笔管的奢丽制作
十二、 释“答”——笔帽的异称
十三、 笔头似“箭 ”
十四、 茹笔
十五、 写书笔
十六、 虞龢《论书表》中的文房论札记
附录一 《简毫与长毫》与王学雷君商榷
附录二 科简与料简
十七、 心同理同:西方的“毛笔”与中国的制作
十八、 古笔研究中的文献引用问题
十九、 读《中国的文房四宝》
二十、 对两则古笔文献的理解
中卷 古笔图说(战国—唐)
一、 战国(楚、秦)
1. 信阳长台关楚墓笔
2. 左家公山楚墓笔
3. 包山楚墓笔
4. 江陵九店楚墓笔
5. 放马滩秦墓笔
二、 秦
6. 睡虎地秦墓笔一
7. 睡虎地秦墓笔二
8. 周家台三十号秦墓笔杆
三、 西汉
9. 江陵凤凰山一六七号西汉墓笔
10. 江陵凤凰山一六八号西汉墓笔杆
11. 临沂金雀山西汉周氏墓群十一号墓西汉笔
12. 西郭宝墓笔
13. 尹湾汉墓针刻漆套竹杆对笔
14. 网疃汉墓针刻短单套木杆笔头一
15. 网疃汉墓针刻短单套木杆笔头二
16. 敦煌马圈湾西汉笔
17. 敦煌高望燧西湖笔
四、 东汉
18. 敦煌悬泉置笔一
19. 敦煌悬泉置笔二
20. 敦煌悬泉置笔三
21. 敦煌悬泉置笔四
22. 汉居延笔
23. 武威磨咀子“史虎”笔杆
24. 武威磨咀子“白马”笔
25. 武威磨咀子汉笔
26. 居延附近发现木笔杆及笔头
27. 乐浪王光墓笔头
28. 汉雕象牙笔杆
五、 东晋(前凉)
29. 旱滩坡十九号前凉墓笔
30. 阿斯塔那画笔
31. 东晋束帛笔头
六、 唐
32. 吐鲁番阿斯塔那墓唐笔
33. 吐鲁番阿斯塔那苇杆唐笔
附 江宁上坊村三国瓷制笔
下卷 汉唐古笔文献辑释
一、 韦诞《笔方》校议
附录:韦诞奏论笔墨事笺
二、 王羲之《笔经》校笺
三、 传为《笔经》制笔语笺释
四、 蔡邕《笔赋》校注
五、 皇象论笔墨札笺
六、 傅玄笔论四篇校笺
七、 成公绥《弃故笔赋》校笺
八、 嵇含《试笔赋序》笺注
附录:嵇含《笔铭》
九、 王隐《笔铭》笺释
十、 虞龢论笔墨事笺
十一、 萧绎《谢东宫赐白牙镂管笔启》笺注
十二、 《北梦琐言》载梁元帝笔事校注
十三、 段成式论笔书二篇注订
十四、 《北户录》所记笔资料两则校笺
十五、 《芝田录》记笔工事释补
十六、 柳公权《谢惠笔帖》小笺
十七、 传李阳冰《笔法诀》注释
十八、 宋代辞书中关于鼠毛与兔毫资料两则笺释
征引文献
后记
精彩书摘
“汉居延笔”的发现、图像与踪迹
1. 发现者:贝格曼
马衡先生(1881—1955)的遗著《凡将斋金石丛稿》 (以下简称《丛稿》),1977 年由中华书局出版,其中有一篇《记 汉居延笔》,是运用“二重证据法”研究古代毛笔的经典之作。 他写作这篇文字的动因,是缘于 1931 年中瑞西北科学考查团在 发掘内蒙古额济纳土尔扈特旗破城子遗址时,发现的一支东汉初 期的毛笔。马衡将它定名为“汉居延笔”,并一直沿用至今。
“汉居延笔”在当时确实是一个重大的考古发现。此前所能见到的古代毛笔实物,最早仅是藏在日本正仓院中的唐笔,没想到这次竟发现了更早的汉代实物。为了向社会披露这一惊人的发现和研究成果,任务自然落在擅长考证的马衡先生的肩上,于是就有了《记汉居延笔》这篇经典之作。据《丛稿》所载《记汉居延笔》开篇文字叙述看,确实透露出马衡先生亟欲向社会披露这一发现的迫切之情:
我国古代之笔之保存于世者,曩推日本奈良正仓院所藏之唐笔为最早,此外无闻焉。不意今竟有更早于此者。爰就研究所得,尽先发表,以介绍于世之留心古代文化者。
在表达完这个愿望之后,紧接着就介绍起发现经过:
一九三一年一月,西北科学考查团于旧蒙古额济纳土尔扈特旗之穆兜倍而近(即破城子)地方……发现汉代木简,其中杂有一笔,完好如故。
这段文字把“汉居延笔”的发现经过,交代得应已很清楚了。本来事情到此可以结束,但笔者多留意了一下文后的编者按语:
编者案此文原载北京大学《国学季刊》三卷一号(一九三二年三月),是西北科学考查团短篇论文之一,又载《西北文物展览会特刊》(一九三六年,南京)。
在好奇心的驱使下,笔者搜到了这期《国学季刊》(以下简称《季刊》),马衡此文排在第二篇。编者按语中还提到的《西北文物展览会特刊》,但其中并未载有此文,盖为编者误记。然以《季刊》所载和收录于《丛稿》中的《记汉居延笔》对读后,却发现了一段被隐没了的史实。
《丛稿》所收录者,乃是从《季刊》所刊原文转录而来,这应该不会有什么异议。可是,两者在开篇的叙述文字上却不十分一致,很明显,《丛稿》收录时是动了手脚的。《季刊》所刊原文在“不意今竟有更早于此者”句后,紧接着有“此诚惊人之发现矣”一句。难道这是作者或编者后来觉得“过甚其辞”,抑觉其“拖沓冗赘”而做的删除?我看未必。在《季刊》所刊原文第二段叙述发现经过的文字中,我们找到了较明确的答案。《季刊》原文是这样的:
二十年(一九三一)一月,西北科学考查团团员贝格曼君(F.Bergman)于蒙古额济纳旧土尔扈特旗之穆兜倍而近地方……发现汉代木简,其中杂有一笔,完好如故。
按:“二十年”即民国二十年,公元1931年,《丛稿》只取公元纪年。最主要的是,《丛稿》将原文中西北科学考查团“团员贝格曼君(F.Bergman)”彻底删除了。这样一来,历史昭示给后人的“史实”就变成:发现“汉居延笔”的功劳,是属于西北科学考查团的“集体功劳”,而不属于个人——贝格曼。在数十年后的今天,再来看这样的改动,确实有些匪夷所思,好好的一个贝格曼,他的功劳却硬生生地被剥夺了。
贝格曼这个名字对于今天的人们已有些陌生,但他确实是一个不容忘却的人物。贝格曼全名沃尔克·贝格曼(Folke Bergman,1902—1946),瑞典考古学家。1927年1月,贝格曼刚从大学考古专业毕业,毕业论文是研究十二三世纪北欧海盗铭文。但一个电话,竟改变了他的命运:瑞典国家文物局负责人柯曼博士询问他,愿不愿意到中国西部做至少一年半的考古探险?那时,斯文·赫定正与中国同行筹建中国西北科学考查团。考查团设置了一中一外两个考古学家的位置,贝格曼没有放过这难得的机会,和中国学者黄文弼一同成了考查团的成员,这样竟然度过了八年的青春岁月。1927年至1935年,贝格曼三次往返于中国西北的内蒙古、新疆、甘肃,行程数万里,三分之二的旅途靠骑骆驼或步行,所到之处大部分地区当时无人定居。在此期间,他考察了三百一十处古迹、遗址,发现了举世闻名的“居延汉简”和“小河古墓”。1946年,贝格曼因病去世。
至于贝格曼“发现汉代木简,其中杂有一笔”的发现细节,杨镰先生为我们做了生动详尽的描述:
1930年,贝格曼在内蒙古额济纳旗——汉代居延边塞——发现了万枚以上的汉简,使学术界为之震惊。当时有人将这一成就与打开敦煌藏经洞,并列为中国20世纪两大考古发现。关于居延汉简,有这样一个细节:贝格曼在蒙古族牧民陪同下,考察烽燧。在破城子遗址,他注意到地面有许多老鼠洞。他们带的一只狗穷极无聊,开始追逐老鼠,老鼠钻进洞,狗一不留神也出溜进去,进去容易,出来就难了。为解救这只狗,挖开了老鼠洞穴,立时大家全惊呆了:延续使用了千年之久的老鼠洞就像迷宫,其中布满了完整与残缺的汉简,那是一代又一代勤快的老鼠拖到家中储存的粮食与磨牙的用具。贝格曼在笔记中管这里的老鼠洞叫“汉简陈列馆”。此后通过不懈努力,竟出土了成吨的木简与其它文物。其中包括可能是中华文明史最初的纸,以及一支汉代毛笔的实物。日本人即将占领北平之前,“华夏第一笔”与北京猿人的头骨,一起神秘失踪,但汉简完好保存下来。
1931年至1933年期间,贝格曼在北京协助马衡、刘复等人对额济纳地区出土的文物进行整理编号。只因了他发现的“汉居延笔”,马衡才能写出《记汉居延笔》这篇经典之作。可为什么在后来却隐没原本应当属于贝格曼个人的功劳呢?事情到此还没结束。
马衡先生于1955年就去世了,这本《丛稿》并非他本人编定。因此,剥夺贝格曼功劳的“嫌疑人”应该是编者。中华书局编辑部在“编辑后记”中提到,始终整理编次《丛稿》的人是傅振伦。根据这个线索,笔者找到了傅先生的一篇总结马衡学术贡献的文章,完全印证了“后记”的说法:
一九六五年我整理了马先生的文集——《凡将斋金石丛稿》(1977年由中华书局出版)……
傅振伦(1906-1999),河北新河人,是我们并不陌生的一位学者,曾参与额济纳河畔西汉烽燧出土的竹木简牍的登记、整理工作。他与马衡的关系是学生兼同事,可他删削马衡原文并非“无意”,但确实有着深层的原因。提请读者注意,傅振伦先生说他整理《丛稿》的时间起始于1965年。第二年,“文化大革命”爆发,《丛稿》从此延宕至1977年方得出版,虽然这时“文革”已经结束,但人们的思想还没有完全扭转:马衡“复出”了,而贝格曼还定格在“资本主义学者”的框框内。我们完全相信傅振伦先生是一位正直的,有着强烈学术使命感的老学者,不然他也不会在“文革”刚结束,就迫不及待地将乃师马衡的遗著出版,贡献于学界。
“汉居延笔”是由瑞典考古学家贝格曼发现的,向社会披露发现经过、发现者和介绍这支毛笔的是马衡先生。我们从文献史料中探明了这段被隐没的史实及其原因,然而这支毛笔的“身影”和“真身”又如何呢?
2. 图像与踪迹
在《记汉居延笔》中,马衡先生对“汉居延笔”的形制及制作工艺进行了详尽细致地描述和考证,但《丛稿》没有提供图像。这或许是受到当时印刷条件的限制,而产生的又一个无奈之举。前引杨镰先生的文章说,日本人即将占领北平之前,这支“华夏第一笔”与北京猿人的头骨一起神秘失踪,但汉简完好保存下来。那么,“汉居延笔”果真如北京猿人头骨那样真的“神秘失踪”了吗?我们先从它的图像说起。
马衡先生发表于《季刊》上的《记汉居延笔》原本是有图版的,可是只有这支毛笔的半截图像,左边还附有比例尺。检看全文,发现编辑上的一个疏漏:这半截毛笔图像标为“图二”,而漏登的“图一”按理就应该是全图。杂志既已出刊,再重新刊上,势不可能,那么只有采取“一稿多投”的方式或许可以弥补。在1934年的《艺林月刊》上,我们再次读到了这篇文字,其中“贝格曼”写作“贝格满”,只是译音不同而已,重要的是“汉居延笔”的“全貌”被展示出来,然而旁边的一行图注却再次让人失望:
仿制汉居延笔(西北科学考查团理事会赠)。
《艺林月刊》是民国时期北平中国画学研究会主办,艺林月刊发行所发行的美术类刊物,相较于学术性很强的《季刊》,这个刊物则较为普及,读者自然面广量大。通过它把《记汉居延笔》再刊登一次,可能对“汉居延笔”及其发现的信息传播,效果或许更好。那为什么它只刊登仿制品,而不用原件图像呢?我们发现,马衡的这篇文章并非其本人提供,而是和他一起整理居延汉简的同事、语言学家刘复(1891—1934,字半农)誊写后交给《艺林月刊》的,文末还有刘复的识语:“中华民国二十一年西北科学考查团理事会印行刘复写。”关于“汉居延笔”的仿制品,傅振伦先生有所回忆:“考查团理事会还把‘居延笔’由北平琉璃厂复兴斋小器作铺制作樟木笔杆的模型,盛以楠木匣,并由刘复仿唐人写经体写成古色古香的黄纸卷子,同时出售。”《艺林月刊》所刊出的图像,正如图注所标明的是西北科学考查团理事会的仿制赠品。或许可以这么认为,仅刊登仿制品并无妨于读者对“汉居延笔”的认知,同时隐隐地提示读者仿制品是可以“出售”的——反正不是“纯学术”读物,无形间起到了广告的作用。
当年“汉居延笔”的仿制品,现今在市面上偶尔还能见到,正如傅振伦所回忆的那样。但我们还是希望见到它完整的真实“身影”。
正因为有马衡先生《记汉居延笔》,我们对这支充满传奇色彩的汉笔似已十分了解,尤其是在研究或介绍古代毛笔时,都不会将它遗漏。但它的图像资料却很少见到研究者引用,描述也多是转述于马衡的文字。在1949年后,中国大陆地区出版的专业图录中,“汉居延笔”的图像在20世纪80年代早期的《笔墨纸砚图录》中有较明晰的展示,但以今天的眼光看,这张图版效果已非常不能令人满意了,而且没有标明来源,因而可以认为有可能的是从民国时期的出版物上翻拍而来。有些奇怪的是,这张聊胜于无的图版似又从不为研究者所注意,大概还是缘于图版效果本身的原因吧!
在文物考古研究中,线描图的作用是不言而喻的。许多研究者为说明器物的细节问题,宁可采用线描图,也不用原物照片,何况图版本身或印刷制作上可能还会出现的种种问题。作为一件器物,“汉居延笔”自然也拥有描绘它的线描图。绘制线图是考古学家必须掌握的一项技能,最早为“汉居延笔”绘图的自然是贝格曼,他在《考古探险笔记》中就附有一张较为传神的图片,应该为其本人所绘。另外,钱存训先生的名著《书于竹帛:中国古代的文字记录》图版二八(丙),也附有线图,但相较贝格曼所绘,则显得有些含混。总之,贝格曼所绘,更值得研究者重视。
“汉居延笔”的图像,或说是它的“身影”,总算或明或晦地保存了下来。但原件,或说是它的“真身”,是否就如北京猿人头骨那样谜一般地消失了呢?
贝格曼发现的居延汉简现藏于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该所研究员邢义田先生曾细致考证过这批简牍的“迁徙史”:自从贝格曼发现居延汉简以后,1931年5月底即运往了北平,藏于北平图书馆。最初由北京大学教授刘复、马衡代表中方参加整理和释读工作。1937年7月,卢沟桥事变爆发。7月28日,日军占领北平。在日军的威胁下,考查团理事会干事沈仲章,在理事徐鸿宝的协助下,秘密将简牍和相关资料自北平运到香港;其后,再从香港地区运到美国;1965年又自美国运回台湾地区。“汉居延笔”与简牍是一起发现的,也是一同运往北平的,之后是否也是经香港地区、美国,最后落脚于台湾地区了呢?邢义田先生的另一篇考证给了我们一个明确的答案——“此笔原件现藏史语所,并在文物陈列馆长期展出”。他还毫不吝惜地提供了一张图版,使我们看到了这支“华夏第一笔”至今最为清晰的图像,并寻到了它的踪迹。
写书笔
六朝隋唐佣书业之兴盛,时贤论之已详 ,唯于相应之抄写工具似未究心。王羲之虽古今“书圣”,然其平时所读书,亦必谋诸写书之人,不能亲为也。其一帖云:“下近欲麻纸,适成,今付三百,写书竟访得不?得其人,示之。”“写书”指抄书之人,即佣书者也。而佣书者所用之笔,当与羲之平素所用之笔当有别,即所谓之“写书笔”也。唐段公路《北户录》卷二“米饼”条:“且前朝短书杂说即有呼……笔为双、为床、为枚。墨为螺、为量、为丸、为枚。”崔龟图注:“《梁令》云:写书笔一枚一万字。”按《梁令》,南朝蔡法度等撰,三十卷,大抵因《晋令》而增损之。原书已佚,崔注乃其佚文。周一良先生考古人写字速度及写书人用笔之规定尝引及之。曰:
古人写字速度,据《魏书》五五刘芳传,“芳尝为诸僧佣写经论,笔迹称善,卷直以一缣,岁中能入百余匹”,是则约三日写一卷也。《周书》四二周大圜传,“梁武帝集四十卷,简文集九十卷,各止一本……大圜……乃手写二集,一年并毕”。所述与三日一卷之进度亦相近。写书人用笔之规定,《侯鲭录》载梁令云,“写书笔一枚一万字”,盖魏晋南北朝时一般如此。
周氏据《侯鲭录》乃北宋赵令畤所作,赵氏所引《梁令》疑亦据《北户录》崔注,然崔注先见,考镜源流,自宜引崔注。本文所关注者乃“写书笔一枚一万字”也,缘此条资料可贵之处有二:
一、 古人于笔罕有记载其耐书写之字数,而多载其易耗。如《非草书》“十日一笔,月数丸墨”、郑灼家贫“抄义疏,以日继夜,笔毫尽,每削用之”等。至于字数,北宋章子厚(惇)《论书》云:“张侍禁笔甚佳。一管小字笔,写二十万字,尚写得如此,是少比也。”此似过甚之例,然《北户录》卷二“米饼”条崔注引郑虔云:“麝毛笔一管,写书直行四十张。狸毛笔一管,界行写书八百张。”于字数亦不明确。试以最标准之写经纸一纸二十八行,行十七字记,则狸毛笔一管写书八百张,可写三十八万余字。东瀛士流一循唐制,其《造东大寺解案·写经所物资提供文类》中有“菟(兔)毛笔六十二管,以一管写纸百五十张”“堺(界)料鹿毛笔六管,以一管堺纸一千六百张”及“题料狸笔七管,管别题百卷”之记载,亦以最标准之写经纸字数推之,则其兔毛笔一管可写七万一千四百字。是知章子厚谓“张侍禁笔甚佳”,盖非夸饰也。而《梁令》“写书笔一枚一万字”,似最为实际,故周氏谓“盖魏晋南北朝时一般如此”,是其有普遍之价值,非极端之例证。第不知南北朝时期之制笔技术及材料之选择上,尚不如唐宋耶?是亦有待深考者也。
二、昔人每喜言笔,名品佳制时见载录,而“写书笔”者似仅见于此。顾名思义,“写书笔”即专用于抄写书籍之笔,当与其他笔有所不同。据此,知六朝时期笔墨尚有专制,非泛泛施用也。另按:日僧空海于弘仁三年(812)上《奉献笔表》,其中提及狸毛笔四管,三种为真、行、草三种字体而作,一种则专用于“写书”。可见“写书笔”自是固有之名称,其与一般之笔当有所不同,应较他笔更利于抄写。他若虞龢《论书表》所记张永所造之“草书笔悉使长毫,以利纵舍之便”,则与写书笔显有别矣。除此,崔龟图注又云:“宋元嘉中,格写书墨一丸,限二十万字。”唯不知此是否亦采自《梁令》?然有“写书墨”,知此种墨亦专用于抄写书籍也。顷读王元军氏《六朝书法与文化》,其参考周文,而将《梁令》以意读作“写书,笔一枚一万字”,如此则隐没世有“写书笔”此种毛笔之事实,而崔注“格写书墨一丸”又将如何句读耶?故于此揭出,供商榷焉。
本文揭出“写书笔”,非惟就事论事,实有感于古今论笔者多着眼于笔与书法艺术之关系,而笔之用于抄写之本质越来越受忽视,此种趋势已无可避免,亦势之使然耳。由此,或可瞻前曰:盖汉末六朝以前,书法尚未大兴,尤以纸张未普遍用于书写之时,于狭长之简牍上写字,笔头不宜过大。在非特殊情况之下,笔之形制较为单一,所书字体亦较单一,且足于用,即无所谓此是“写书笔”,彼是“书法笔”也;而顾后则曰:汉末六朝书法大兴,尤以纸张开始普遍用于书写,而字体样式繁多,表现形式亦意态纷呈,如空海《奉献笔表》即举出真、行、草三种字体。于是,笔之形制开始相应地繁多起来,所谓之“写书笔”便凸显出来,渐与“书法笔”犁然有别矣。而后世科举考试所用之“摺笔”,盖即写书笔之类,与书家写真、草、篆、隶所用之笔,亦犁然有别矣。或可谓,写书者与书法家之不同,由各自所用之笔即可体现;中国文字之实用性与艺术性的区别,亦因笔之形制不同而得到体现。
前言/序言
序二(薛龙春)
无论是从创作还是从研究的角度,对于书写的物质环境,我都一直抱有浓厚的兴趣。书写的工具、材料、操作空间、展示空间,这些都是与创作活动密切相关的问题。尤其是笔毫的刚柔、长短、粗细与书写方法之间的关系,笔与字的大小、字体、风格之间的关系,都值得深入探讨。但说实话,对于古笔的选料与制作工艺,我一直茫然莫识其梗概。而在过去较为粗疏的书史研究中,人们大多从风格的角度出发,对于历史上的书写活动进行规律化——却不免简单化的分类。之所以说简单化,就是因为研究者很少关心具体的物质环境,筑基于此的种种分析活动,自然因缺少历史性而难以取信于人。那些抽象的形式与风格研究虽言之凿凿,但一放到具体环境中加以论证,则马上显得似是而非。当艺术社会史研究、文化研究在书史研究领域逐渐崛起之后,人们开始重视具体个案的研究。大量的新成果显示,艺术风格的变迁不仅是形式的逻辑发展,也不仅是所谓的时代风气的结果,它与物质环境的缓慢变化也有千丝万缕的关联,这其中的复杂性,远非“点、线、面”或是“晋人尚意、唐人尚法”之类的标签可以解释清楚。相应地,物质环境、物品文化也开始成为颇具魅力的议题。关于古代建筑、家具、礼仪、书写工具与材料的研究成果,不仅提供给书法史界大量“新知识”,也成为我们重构书写活动、解释书法风格与旨趣的新动力。比如,藏头护尾、笔笔中锋的技术要求,横平竖直、涩进持重的趣味,不仅与碑学的审美倾向有关,也与羊毫、生宣的物质性互为表里。然而我们又必须认识到,藏头护尾、笔笔中锋并非书法与生俱来的内在规定,而是后代一种积极的文化建构。在硬毫笔流行的年代,八面出锋、惊蛇出草才是人们对于书写技术与境界的诉求。相信在孙过庭看来,藏头护尾、笔笔中锋未免聚墨成形之诮。但在包世臣的笔下,“筋骨血肉”却被重新阐释为有利于碑学主张的话语。显然,如果我们离开工具、材料在明清之际的激烈变动来讨论清代碑学,对于包世臣的理论主张必然难喻其旨。
相关推荐
— 没有更多了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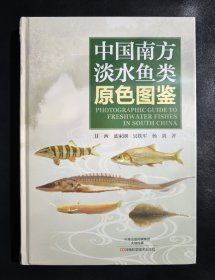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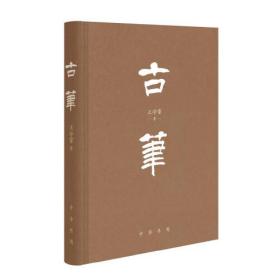

以下为对购买帮助不大的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