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正版现货新书 制造好人 9787536088764 陈集益 著
全新正版现货,以书名为准,放心购买,购书咨询18931383650朱老师
¥ 22.25 5.6折 ¥ 40 全新
仅1件
作者陈集益 著
出版社花城出版社
ISBN9787536088764
出版时间2019-05
装帧精装
开本32开
定价40元
货号1201889322
上书时间2024-12-19
- 在售商品 暂无
- 平均发货时间 9小时
- 好评率 暂无
- 最新上架
商品详情
- 品相描述:全新
- 商品描述
-
作者简介
陈集益,1973年生,浙江金华人。高中毕业后做过多种工作,2002年起“北漂”至今。曾于鲁迅文学院不错研讨班学习写作。作品发表于《十月》《人民文学》《钟山》《花城》等刊物。出版有小说集《野猪场》《长翅膀的人》《哭泣事件》《吴村野人》。曾获《十月》新锐人物奖、2009年度浙江省青年文学之星、2012-2014年度浙江省很好文学作品奖、第三届青年产业工人文学奖等。现供职于青年文学杂志社。
目录
土地里能长出现代性吗?(自序)/ 陈集益制造好人驯牛记金塘河侍候狗特殊遭遇打开时代与历史的魔盒(访谈) / 陈集益 张鸿
内容摘要
《制造好人》收入了陈集益近年创作的六个中短篇小说。作者致力于书写个人独特的生命体验、心灵记忆,以此反映时代洪流中人的生存处境。《制造好人》是荒诞时代的现实折射,也是人性的集中表演。《金塘河》中一心想要脱贫致富的父亲堪比海明威笔下的硬汉桑提亚哥,蕴藏着惊人的情感势能和思想张力。《驯牛记》和《狗》借动物说人,寓意深远。《侍候》和《特殊遭遇》写底层人的血泪挣扎,是与身俱在的痛与思。书中作品从艺术表现看多有魔幻现实主义味道,从思想性角度看则属批判现实主义。其字里行间既有文以载道的传统,又葆有先锋文学的遗韵,从而使小说所产生的审美与意蕴,超越了社会现实和故事本身,呈现出异常复杂的况味。
主编推荐
1、《十月》新锐人物奖、浙江省很好文学作品奖获得者陈集益力作。2、陈集益的小说兼有莫言的雄浑,阎连科的荒诞,余华的幽默。3、现代性五面孔丛书旨在推崇现代性写作,拒绝平庸叙事。
精彩内容
制造好人(节选)制造好人的机器真的要运来吴村了,这事让我很是紧张。这机器是怎么回事,能不能制造出好人,是怎么制造的,我一概不知。接到通知时,乡里的刘干事只说有一台榨制什么的机器要运来吴村了,务必配合省城来的朋友搞好这次工作,他们是省里什么协会某某主席的哥们。我有些受宠若惊。我只是一个小小的村委会主任,可我要接待的是省里来的、什么主席的哥们,这是多么光荣而艰巨的任务。我答应刘干事说:“放心吧,刘干事,我会好好招待客人的。山里需要榨制的茶籽、桐子、油菜籽多着呢,机器不会闲着的。只是,收费多少合理呢?”刘干事说:“从省里运来的可不是榨油机,而是一台制造好人的机器。陈哥你不是在装聋作傻吗?”我蒙了,这样的机器于我而言闻所未闻。在我的追问下,刘干事在电话那头不痛不快地说,那机器其实是省里几个艺术家搞的什么行为艺术,他们要找一个地方实验“制造好人”,托人找来找去,就找到了我们这偏僻地儿。我不清楚行为艺术是个什么玩意儿,当年在学校,艺术总与美术、音乐、文学联系在一起,那是很好高深、离我们很遥远的东西,但是直觉告诉我,“制造好人”绝不会是什么好事情,难道好人是能够制造出来的吗?我把我的想法跟刘干事说了。刘干事说:“陈哥,我不是提前跟你说了嘛,制造好人是一项行为艺术,行为艺术你有听说吗?我查了资料,说它是一种在特定时间和地点,拿身体表演的艺术。大概跟杂耍、杂技,移形换位、大变活人差不多吧……”在这之前,我接待过形形色色的人,有老干部来山里疗养的,有专门驱车到井下村再步行上来吃野味的,有本地小有名气的画家带着学生来写生的。但是恕我直言,我不太想接待这次要来的人,省城那么大,难道就没有这帮猢狲的用武之地吗?干吗跑到大山里来?但是我也不想得罪刘干事。尽管他在山乡也就是跑跑腿的角儿,恐怕连古戏中的九品芝麻官的部下都算不上,但是你得明白,当他通知一个什么事情要我去做的时候,他代表的是整个山乡政府。一旦他把我拒不接待贵宾的事情上报给乡长,那么我就再也不可能审批出木材用于买卖了。而我,那几年赚钱的主要方式是贩卖木材。所以我挂了电话,就决定把我们村的大会堂腾出一个地儿来,同时差几个青壮年去把机器抬回来。那时候绕着山乡水库修建的公路虽然延伸进了大山,山里人来往于山乡政府和汤溪镇方便多了,但是由于资金匮乏公路修到井下村就搁置了。从井下村到吴村有五里地的泥泞路,该路修筑在溪边田坎上,就像被洪水冲上岸的一根烂猪肠—我派去的几个人在这路上奋战,庞大的机器压断了好几根硬木杆子,还把一个人的脚指头砸伤了,天黑之后他们垂头丧气地回家,每人身上披着一层白剌剌的盐。第二天,才有机灵人带了几根碗口粗的圆木垫在机器下面,圆木随机器的推移一根一根交换着当轮子使用,这样才将机器一步一换地挪到了村口。机器一共由三部分组成:部分是一把冷冰冰的铁制椅子,椅子靠背上方悬着一个黑色的罩子,罩子上有密密麻麻的电线、管线、电容、小零件,其中有一部分电线管线连着机器的第二部分—那是一个立式的柜子,上面装满各种奇怪的仪表、指示灯、按钮,没有猜错的话,它应该是整台机器的控制台—而机器的第三部分是横卧的,它状似一口密封的棺材(后来知道它叫制造舱),机身和机盖都由乌黑发亮的铁板焊接而成,焊接处可见成排的焊钉,好似一只只黝黑发亮的牛蜱虫;它是三个部分中体积很大的,应该也是很重的,看样子接近可以躺下一个人;比如,人头搁在机器宽的那一头,人脚搁在机器窄的这一头—它的两头,都从里面伸出来很多管子,管子颜色和质地各不相同……不瞒你说,我也是一个初中生,山乡初中毕业的,在当年的吴村也算是一个有文化的人,可是由于回村务农多年,泥土代替了课本,我已经把有限的一点物理化学知识都忘掉了。我看不懂它的构造原理,就像我想不明白:那几个省里来的猢狲为何要制造出这样一套怪模怪样的机器,它到底干什么用?真的能制造出好人?还是仅仅用于“移形换位、大变活人”的道具?—我仔细地端详,它稳健、牢固、严实又不失实用,我想当一个人躺进这样一个冰冷、压抑、封闭的容器,他一定会感到无端的恐惧。那么村里谁会个躺进去供他们做实验呢?我有些后悔了,后悔答应刘干事接待这帮子人。他们一共四个,三男一女,男的有两个留着长发,有一个染着烫过的黄毛。他们穿着花花绿绿或者方格子衣服,戳有破洞的牛仔裤紧勒着结实的屁股,反而那女的剪了一个毛寸头,穿的衣服是亚麻布的,松松垮垮,看不见胸也看不见臀。他们讲普通话,一个戴眼镜,一个戴墨镜,一个扎耳环,一个手持摄像机。他们对农村充满好奇,据说大伙儿嗨哟嗨哟搬运机器的时候,他们在田野里为看见一只蝴蝶而欣喜。当机器运抵目的地,我慌慌张张跑去迎接,满脸堆笑,看见他们正围着一堆牛屎戳戳捣捣,嘻嘻哈哈。我本打算安排他们去我家里吃住的,就像以前招待城里来的老干部那样,杀鸡宰鹅下河摸鱼。看见他们那副相互打闹、对我有失敬重的样子,就改变了主意。我们村的大会堂是一栋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建造的土木结构建筑,在大集体时期,“社员们”在这里吃过大锅饭,开过会,观看过样板戏,那时候常有驻村干部在这里居留,生火做饭。现在它破败了,不过用条石垒成的大门顶上,那颗红五角星依然清晰,墙壁上的“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等标语也没有褪去。我安排他们住在大会堂里。然后返身去家里为他们弄点吃的来。当我背着米和菜回来,在大会堂门口,出现了多年前电影队来村里放电影那般的场景,男男女女,老老少少,从黑乎乎的门洞里拥出,将大会堂围了个水泄不通—这些人是来做杂技的吗?这是啥玩意儿?干什么用的?尽管村里人早已听说有一台制造好人的机器要运到村里来,可是面对实物谁都不愿或者不敢相信这是真的了。此刻为什么要制造好人的疑惑,就像一块靠近火光快要流脓的冻疮,奇痒无比,而我的回答却挠不到痒处。因为我并不比他们了解得更多。第二天,机器就嗡嗡嗡地响起来了。机器上的指示灯一闪一烁,有六七种颜色,颜色亮起时还会发出嘀嘀声。那四个人早早地换上白大褂,在大会堂里忙乎着。他们用一块印有宣传图样的布帘在大会堂中央隔离出一个工作的区域,几张曾经用于开会的桌子上摆满了貌似医疗器具的东西。一些人围着看布帘上的孔繁森、焦裕禄、邱少云、黄继光、雷锋、董存瑞……以及“讲道德、做好人、树新风”“克己奉公,助人为乐”等等标语。就在标语旁边,另一些人在叽叽喳喳着:井下村就不造吗?为什么要到我们村来造?我们没有理由成为试验品呀。我躲得远远的,因为我不能说出:这是省城什么协会主席的什么哥们在搞什么行为艺术;因为刘干事有交代,在机器撤离吴村之前是不能将真相告诉村里人的,否则实验无效,数据不真实。还说:只要做到严格保密,机器撤离后他们将给予每个进入机器的村民一百元钱奖励—这是一笔不小的报酬!对于那时候的吴村,可以让一个老人吃上一个季度的大米。这事看起来不坏,到任务完成、分发报酬之日我再向“好人”们摊牌即可。更何况,这次接待任务完成之后我个人肯定也会有一些好处的,比如多少能从山乡政府批到几百立方米的树卖吧?这么多年来,我确实每年都能从山乡政府拿到砍树指标,而别人是不允许私自伐木拉到山外去卖的。就算伐了,请不来木材检查站的公职人员在每棵树上敲上检查站的钢印,是运不出山的。其中的互惠互利及微妙关系,也只有亲历者才能体会。所以临近中午,我发现大会堂里除了一些孩子追来跑去地玩游戏,大人们大多去田地里忙活了,留下几个老人、懒妇与闲汉也没有一个肯把自己“交出来”—我就有些不悦了。我所急的,倒不是村里人拿不到一百元钱、丧失一次进财的机会,而是怕制造好人的机器过于被冷落,“好人”一个都“制造”不出来—到时刘干事要问罪于我。“社会需要好人,好人需要制造”“人的生命是有限的,为人民服务是无限的”“一个国家,一个政府,任何时候都不能缺少好人。只有好人越来越多,社会才能越来越好……”那几个所谓的艺术家已经不像昨天那般轻浮了,他们在白大褂之外戴了“制造好人”的红袖套,坚持不懈地宣扬着制造好人的必要。但是那些留下来仅仅为了等着看热闹的听众一脸茫然,他们几乎不听或者听不懂普通话。我想总得有个人带头走进机器,至少有一二十人响应才好。我说:“你们能不能严肃一点,排好队配合一下制造好人的工作?”我是用商量的口吻说的,结果出乎我的意料—他们说:“我们现在就很好了啊,从不干坏事,要是个坏人还敢坐在这里吗?”我说:“要是好人就更不怕进机器了。”他们说:“光把我们变成好人,别人都不变,将来不是明摆着让人欺负吗?”我说:“凡事总有先有后嘛,做好人有什么不好?”他们说:“那你为什么不先躺进去试一下?”我被说得哑口,心虚地溜了。我想实在不行,就由我来做个试验品吧!—如果制造好人诚如刘干事所言,仅仅是在特定时间地点拿身体表演一番的艺术,人进去再出来以后毫发无损,这又有什么?可是,就因为有了要做“个”的想法吧,我对那台机器感到莫名的忌惮了。我有一种奇怪的感觉:它是真的;如果单是行为艺术的道具,何苦造得如此精密复杂呢?
相关推荐
-

正版现货新书 好人难做 9787020090228 红柯著
全新北京
¥ 15.62
-

正版现货新书 宣州好人颂 9787565029424 田斌
全新北京
¥ 30.89
-

【正版】制造好人/现代五面孔
全新嘉兴
¥ 22.15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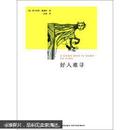
好人难寻 正版现货
九品广州
¥ 22.00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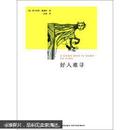
好人难寻 正版现货
九品广州
¥ 78.00
-

正版现货新书 好人徐遂 9787517134572 邵红卫
全新北京
¥ 51.88
-

正版现货新书 好人刘崇和 9787562182696 杨辉隆
全新北京
¥ 12.44
-

正版现货新书 好人总在心里 9787520532402 张庆和
全新北京
¥ 30.24
-

正版现货新书 制造系统 9787560661421 李雪
全新北京
¥ 32.40
-

正版现货新书 制造技术 9787111750864 王磊
全新北京
¥ 31.47
— 没有更多了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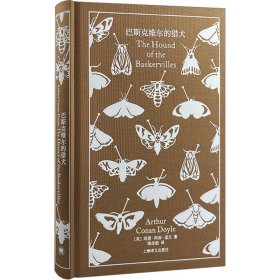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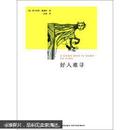
以下为对购买帮助不大的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