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正版现货新书 每天挖地不止 9787559455215 林那北
全新正版现货,以书名为准,放心购买,购书咨询18931383650朱老师
¥ 27.8 4.6折 ¥ 59.8 全新
库存7件
作者林那北
出版社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ISBN9787559455215
出版时间2022-05
装帧精装
开本32开
定价59.8元
货号29399165
上书时间2024-11-08
- 在售商品 暂无
- 平均发货时间 9小时
- 好评率 暂无
- 最新上架
商品详情
- 品相描述:全新
- 商品描述
-
导语摘要
《每天挖地不止》是当代著名作家林那北的长篇小说,将非物质文化遗产“大漆”作为载体,讲述了福建沿海地区一个奇特家族百转千回的故事。从主人公赵定力口中一笔虚幻的财富出发,制造出一个真实的精神事件,将人生小小的痛点出其不意地扩大搅动起来,与古老的历史、人性的深度以及喧哗的当代文化景观紧密交织。
临海的青江村是北宋溃散前遣散到福州的皇族后裔所在地,村里有座罕见的以传统大漆做门的乌瓦大院。年底,大院的主人赵定力去福州城看病,回来后就开始不停歇地挖地。一个家族故事由此展开:酷爱大漆的祖母谢氏,下南洋在槟城谋生的祖父赵礼成、身为满族后代的母亲何燕贞、战争结束前随军舰逃往台湾的大伯赵聪圣……时隔百年,几代人的秘密为何在这时被提起?谢氏死前究竟把装有稀世珍宝的铁罐埋在何处?闻风赶来挖地的人越来越多,乌瓦大院的荒诞故事终将如何收场?缈小的个体能否穿透林林种种,守住生命的本质?
小说以一个百年家族的历史和一个当下的生存故事,把文明进程中必然遭受的断裂、传承、保守、开放、交融、坚守等概念,化为普通人的喧哗与沉默、谎言与伤痛、奇遇与选择,由此呈现中华文明在沿海地区得以保存并走向世界的历史与现实,为读者呈现了一个具有经典气质的文学时空。
作者简介林那北
本名林岚,福建闽侯人,现居福州。当代著名作家,福建省作协副主席,《中篇小说选刊》杂志社社长、主编。已出版长篇小说《锦衣玉食》《我的唐山》,小说集《寻找妻子古菜花》《请你表扬》《唇红齿白》,长篇散文《宣传队,运动队》等二十六部著作及九卷本《林那北文集》。小说被翻译成法、日、俄等语言译介到海外或改编为影视作品。
目录章 铁罐
第二章 个故事:谢氏
第三章 第二个故事:赵聪圣
第四章 挖地吧
第五章 陈细坤回来了
第六章 第三个故事:谢氏与何燕贞
第七章 第四个故事:赵聪明
第八章 蓝花楹与髹
第九章 李翠月啊李翠月
第十章 细米死了
第十一章 打开西髹房
第十二章 大漆门
内容摘要《每天挖地不止》是当代著名作家林那北的长篇小说,将非物质文化遗产“大漆”作为载体,讲述了福建沿海地区一个奇特家族百转千回的故事。从主人公赵定力口中一笔虚幻的财富出发,制造出一个真实的精神事件,将人生小小的痛点出其不意地扩大搅动起来,与古老的历史、人性的深度以及喧哗的当代文化景观紧密交织。
临海的青江村是北宋溃散前遣散到福州的皇族后裔所在地,村里有座罕见的以传统大漆做门的乌瓦大院。年底,大院的主人赵定力去福州城看病,回来后就开始不停歇地挖地。一个家族故事由此展开:酷爱大漆的祖母谢氏,下南洋在槟城谋生的祖父赵礼成、身为满族后代的母亲何燕贞、战争结束前随军舰逃往台湾的大伯赵聪圣……时隔百年,几代人的秘密为何在这时被提起?谢氏死前究竟把装有稀世珍宝的铁罐埋在何处?闻风赶来挖地的人越来越多,乌瓦大院的荒诞故事终将如何收场?缈小的个体能否穿透林林种种,守住生命的本质?
小说以一个百年家族的历史和一个当下的生存故事,把文明进程中必然遭受的断裂、传承、保守、开放、交融、坚守等概念,化为普通人的喧哗与沉默、谎言与伤痛、奇遇与选择,由此呈现中华文明在沿海地区得以保存并走向世界的历史与现实,为读者呈现了一个具有经典气质的文学时空。
主编推荐林那北
本名林岚,福建闽侯人,现居福州。当代著名作家,福建省作协副主席,《中篇小说选刊》杂志社社长、主编。已出版长篇小说《锦衣玉食》《我的唐山》,小说集《寻找妻子古菜花》《请你表扬》《唇红齿白》,长篇散文《宣传队,运动队》等二十六部著作及九卷本《林那北文集》。小说被翻译成法、日、俄等语言译介到海外或改编为影视作品。
精彩内容章 铁罐
一
2019年6月底,赵定力进了一趟福州城。他独自去,说表弟谢玉非病了,其实是他自己病。身体这东西,每一个零部件既然长了,长年累月一成不变地长在固定位置上,就一定有它们各自的道理。嘴是用来贪吃的,屁眼是用来拉屎的,突然吃不香,拉不利索,人再上下不自在,一脚一脚踩下去都是虚的,全身力气都不知去向,不用说,肯定出问题了。什么问题呢?不知道,越不知道越心慌。赵定力忍了一个多月,再忍就没法忍了,于是起个大早。
第二天他才回到青江。
青江不是江,是村子的名字,它临着海,是内海,水面四五百米宽,像一条海的尾巴偷偷伸进来,拐了几个弯后,与一条大江衔接到一起。江水从这个省西北部高高耸起的武夷山灌下来,横穿过大半个省,本来要直接去海里的,半道却被溜进来的海水一把拦住了。每天海水得涨得退,涨时水向西,退时水向东,但海水与江水的交汇地却固定不变,它就在青江村码头附近。站在码头砌得潦草随意的青石板上望去,水面有一道清晰的分隔线,一边浑一边清,一边黄一边蓝,倒也一直相安无事,几千几万年下来像约好似的,从来没有交错浑浊到一起过。码头上密密麻麻排着船。以前船小,看着像一群蚂蚁挤在一起,如今船大了,远远看去仍然像蚂蚁。如果再细看,会发现没有哪艘船是新的,船身上的清漆早已褪尽,船板被长时间水浸日晒后,身体又僵又硬,每一道开裂的纹路都像弃妇幽怨的眼神。从前村里的人并非都捕鱼,闲时也种地,该出海时就出,该下地时就下,海里取回荤的,地里扒上素的,一应俱全,荒年也不怕。但这些年男人女人一个接一个往外走,外面毕竟现钱挣得快,鱼就没人打,地也少人种,就一点点寂寥下来,村子便越发显出了无生趣的老态,日出与日落的演出在这里少了观众,每天都显得懒洋洋的。
村东头是几座山,不高,很柔和地微微上翘,山头彼此相连,拉出一个个柔和的半圆形弧线,看上去就有一股与人为善的谦逊。靠近村子的那座小山丘花瓣般缓缓上扬,周围簇拥着几百亩高低连绵的山地,种着茶、茉莉、果树,就是一些荒掉的地里,杂草也茂盛地连成一片,深浅绿着。整个村子其实就是山的延伸体,从东面向西面倾斜,斜到底,就是那个码头了。而东面半高城上,孤零零立着一棵大榕树,不算特别高,树冠却有五六十米宽,叶子密实有力,彼此互相重叠,树身差不多得两三人才能合抱。离榕树十来米远是一幢三进式的房子,风火墙围出长方形的大院子,墙根砌着一人多高的菱形青石,上面则是用糯米浆、碎贝壳和黄泥巴捣到一起的三合土垒出一尺厚、两米多高的墙体,抹着白灰。马鞍形曲线山墙的墙头上,乌瓦已有一些破碎或缺失了,歪七扭八,但大部分仍结结实实地站在那里,即使有几片已经滑到墙的边沿,瓦身仍显出韧性与硬度,结结实实地支楞出一股谁也不服的气度,举在半空示威着。
整个青江村没有第二幢房子能及它一半阔大气派,也没有哪家用这么黑沉厚实的瓦片,村里人就把这座房子称为乌瓦大院。院子左侧还有一扇拱形偏门,门上方挂简陋的牌子,杉木底、黑漆字,正楷写着:谢婆鱼丸店。大院是赵定力的,鱼丸店也是赵定力的。谢婆则是他祖母,有名字,叫春妹。
已经七十八岁的赵定力是村里的名人。往前几十年,他的伯父赵聪圣和父亲赵聪明比他出名。再往前几十年,他的祖父赵礼成又比赵聪圣和赵聪明更有名。现在赵聪圣、赵聪明和赵礼成都死了,赵礼成死在去马来西亚槟城的海上,赵聪圣和赵聪明本来也应该死在槟城,但后赵聪圣死在台湾,赵聪明则死在乌瓦大院。大院还死过赵定力的母亲何燕贞和个子娇小的谢春妹。建起乌瓦大院的人就是谢春妹,建房的钱则是赵礼成从槟城寄回来的。现在谢春妹死了,赵礼成死了,赵聪圣、赵聪明死了,何燕贞也死了,剩下赵定力。
年轻时赵定力是村里个子的人,高却瘦,主要是骨头细,肉怎么长也撑不起来,看上去就像一条竖起来的带鱼晃来晃去。现在他背驼了,脚也用不上劲——人老不都是从脚开始的吗?腿太长,自然也更容易弯,膝盖往前拱,走起路来背、腰、腿、脖子,浑身到处都是长短不一的弧线。老了,所以病就来了。究竟什么病呢?他得去趟城里的医院。
医生就是表弟谢玉非,比他小十四岁,已过了退休年纪了,却还没正式退。当医生就是这点好,越老越值钱,白发和皱纹都可以拿来当金子贴门面,贴多了,反正不管真假,连自己也慢慢信了。赵定力以前很少麻烦他,一辈子不麻烦才是人生赢家哩。诊室不大,摆一张白色旧桌子,除了谢玉非,还有两个戴眼镜的年轻女孩坐在桌子的对面,也穿着白大褂,但两眼怯生生的,浑身都是学生味,一看就是来实习的。
赵定力在桌子侧面的椅子上坐下,先盯着谢玉非的白大褂看,布已经不太白了,泛着黄,有点皱,袖口那里还微微起了一层细密的毛边。在医院这种地方混久了,自信是靠一个个倒霉的病人、死人赠送的,赠得越多,脸上的自信就会堆得越丰厚,谁还在乎披在外面的一层衣裳?然后赵定力眼光慢慢上移,移到谢玉非脸上——脸皮居然是粉色的,其实是因为白,色素浅,皮底下布着密密的血点,白和红混在一起,就成了粉。像所有的病人一样,赵定力开始惶惶说起自己身体情况,谢玉非问一句他说一句或者三五句,说时眼睛一直盯着谢玉非。表弟脸上在起变化,皮还是粉的,但眉头那里曾一闪而过地微微皱几下。赵定力为什么会注意到这个细节呢?他十四岁那年舅舅来信,说已经生了三个女儿的谢家终于添丁了,早产,只有四斤半。父亲赵聪明于是让他进了一趟城。他提着自家养的两只公鸡和一筐鸡蛋跨进谢家,看到在床上一团小小的肉,脸像宰杀时忘了放血的死猪肉,红得发紫,鼻头堆满星星点点的黄斑,眼紧闭,双拳握住举在肩膀上方抽搐般胡乱舞着,气都喘不匀。这是他次见到谢玉非。
谢玉非说:“你先去做个心电图和血凝全套检查吧,看能不能做肠镜。”
“肠镜?”他嘟囔着,定定看着谢玉非。已经活了七十八年他都不需要做这项检查,突然要查,出什么问题了?人一生下来就明里暗里配齐了各种器官,看上去它们像是为了服务主人而来的,却在几十年里反复向人索要服务,无论哪一个出点毛病都要整得鸡飞狗跳。现在轮到他,他的肠子到底怎么了?
谢玉非笑了笑。“毕竟有年纪了,”他说,“有点毛病很正常。你先去缴钱,然后去抽个血,再查一查心脏。哦,我走不开……”说着他冲对面的实习生抬抬下巴,其中一个清瘦的女孩马上就站起,对赵定力一笑,说:“我是小林,我带你去。”
赵定力只好站起,跟着小林在医院各处走了一圈。几年前他曾来做过青光眼手术,与上次比,医院主楼扩建了,旁边还立起一幢二十多层的新楼,看上去宽阔了很多,但来看病的人却更多。上次挂号、缴费、取药的人挤挤挨挨的,这次更是密集得像是来抢钱,迟一步仿佛就吃了大亏。究竟是生活好了,身体反而更差,还是腰包鼓了,能看得起病的人更多了?不知道,反正乌压压一片,每个有病的身体互相毫不见外地碰来碰去,气息呼来呼去,脸色都不是太好,表情也基本没有。瞅准一个空隙,赵定力边走边侧过头问旁边的小林,他说:“我这到底是……什么毛病?”小林客气地笑笑,说:“先查一下。”
赵定力突然发现笑这东西真是再恐怖不过了,刚才谢玉非的笑,现在小林的笑,都有一层阴森之气,嘴像一口深不见底的井,根本不知道里头究竟藏着清水还是浊泥。他觉得这样不行,得继续问。他说:“要多久才能查出来?”小林说:“不用太久,一两个小时吧。别急,您先安心等着。”
能不急吗?她越说别急,赵定力越急。但急又如何?消化内科诊室外的走廊上有几排蓝色塑料椅,抽过血转回来后,小林让他坐到那里等着。两个多小时后,报告单出来了,谢玉非低头看一眼,说:“你身体素质不错啊,比预计的还好。那就做个肠镜吧。”
赵定力眼虽看着谢玉非,视线却是虚的。他注意力在脑里,脑里正把谢玉非刚才说的话又细细过了一遍。医生这个职业某种程度上跟演员是相似的,越老的医生在病人面前就越能演,尤其是当这个病人偏偏还是医生的表哥……亲情在这时候显得多么奇怪,特别近又非常远。赵定力吸一口气,他说:“你什么都不用瞒我……究竟我有没有问题?话直接说,我也好安排剩下的日子。”
“说什么话啊!”谢玉非打断他,又笑起,“你看你,还是老毛病!这都还没查呢,怎么就有问题了?你这样还真应该尽快查一一而且,鉴于你家的情况,还是查一下好。有病就治,没病就放宽心。有麻药的,别紧张。哎,这两天在家你都吃些什么?”
赵定力说:“我没吃什么,我吃不下……”
谢玉非打断他:“我的意思是吃什么油腻的东西吗,鱼呀肉呀之类?”
赵定力愣愣地看着他,半晌才摇头,“鱼肉都不想吃,吃了就乱拉,拉完又几天不拉。”
谢玉非说:“既然这样,我看就干脆直接做了吧,晚上不用回去一一噢,我家也可以住。我安排下,争取明天早上就查了。”
“这么急?”赵定力感觉到问的时候自己舌头都有点打结。
谢玉非边在处方签上写着边说:“也不是有多急,你既然来了,索性就查了吧,免得到时候还要再跑一趟。一会儿我就下班了,你先在外面等着,到时跟我车一起走。”说着他把处方递给对面的两个实习生。赵定力跟着小林出门,缴了钱,取了药,然后等了一阵,太阳落下去后,真的就坐谢玉非的车回去,在他家住下了。
谢玉非是一年多前刚搬到这里的,是个别墅区,全部是独栋、双拼或者联排的房子。谢玉非把车停在一户带有四五百平方米草地的独栋别墅前,到处是花,院子外圈围起的篱笆上,紫红色的三角梅和橘红色的炮仗花已经开始攀爬,人口则是一道挑高的拱形门,两旁黑色大理石砌出来的方形大立柱上,端正立着两盏古铜色的欧式复古灯。赵定力在进门前迟疑地停下,以前只在电影电视里看到外国人住这样花花绿绿的房子,居然近在眼前的谢玉非家也这样了。谢玉非笑起,说:“这全是小娥弄的,这边房子还在建哩,她就提前雇人把谢家大院后花园里的树能移的都移了过来。人搬个家都累半死,她却让树也跟着搬,就是吃饱给撑。”赵定力点点头附和,心里却一阵诧异。谢家大院花园居然有这么多树?他完全没有印象了。
小娥是陈小娥,谢玉非的妻子,以前是中学语文老师,圆脸,中等个,架一副眼镜,看上去跟普通路人没有两样,没料到种起花草来竟这么洋气。于淑钦有一阵也喜欢种花,但只是用检来的大小不一的盆盆罐罐胡乱种,哪像陈小娥这样有章有法成规模地种,就如同都是钢筋水泥堆出来的房子,城里这些别墅和村里胡乱搭起的房子哪能是一回事?乌瓦大院后院比谢玉非家这个院子大,要是按陈小娥这种捣鼓法,非得弄成小公园,而于淑钦想到的无非种点菜罢了。青江村离城里二十公里左右,这么近,很多东西还是不一样。
这个房子赵定力是次来。十多年前,市里把唐朝时开始陆续兴建的坊巷格局的南后街全拆了,弄成旅游景区,整天挤满人,慢慢周围的街坊也被圈人,包括跟南后街只有一路之隔的青灯巷。谢家的老房子就在青灯巷口,两千多平方米,前后共五进,拆迁时补偿了一大笔钱——究竟多少,赵定力其实并不知道。房子拆之前谢玉非曾打电话问赵定力要不要去看看?赵定力脱口问看什么?谢玉非顿一时,半晌才又重复一句:“你确定,真的不来看吗?”赵定力没有犹豫,还是说不看。那幢房子这几十年里他已经去得越来越稀疏,但毕竟是熟悉的,还有什么稀奇可看的?过一阵就听说谢玉非买别墅了,听说而已,听过就丢脑后,现在一看,还是一惊。得花不少钱吧?是拆迁补偿了很多钱,还是谢玉非本来腰包就很鼓?
谢家大院是谢氏的父亲谢瑞林置下的,前院是春来药铺,一格格药柜子顶天立地围成一圈,谢瑞林在药柜前摆着桌子坐诊替人看病,开了方,旁边直接抓药,左右手都赚钱。院子后面还有四进,则是住人。已经传了几代,每代各自分家,房子早就不是当初的气象了。大部分人几十年前拖家带口去了台湾,美国、北京、上海也另有几支,后留在老房子里的只剩下谢玉非一家。但房子要拆时,各房都派人从各地回来处理房产,却没有哪一片瓦哪一块砖跟赵定力有关,谢玉非多让他去看看,有什么可看的?他不去。细算起来,谢玉非的父亲是赵定力的表舅,表舅的父亲就是赵定力的舅公谢乐施,赵定力祖母谢氏的大弟。也就是说对于那幢前后五进的大院子来说,赵定力和谢玉非一样,都是第四代子裔,理论上老房子跟赵定力也不是一点关系都没有,但政府给老房子拆迁补偿,赵定力却啥好处也没得到。现在他有病了,去得到老房子那么多好处的谢玉非家里住一住,确实也不算什么过分之处啊。
陈小娥很晚才回来,她退休后被私立中学聘去上课。说到底还是有学问好,社会越正常学问越管用。他们只有一个儿子,在美国读博士,刚结婚,娶了个同样在那边读博士的上海女孩做妻子。这些都是谢玉非的底气,一家人没一个季种,谢家嫡传下来能混成这样,也算祖上积德了。但祖上对旁枝爱理不理,谢氏从城里嫁去青江村,运气似乎就被谢家截留了,赵定力现在什么都没有。
住在谢玉非别墅的这一夜,赵定力基本上没有合眼。早上从乌瓦大院出门时本来跟妻子于淑钦说好当天就回去,结果没回,竟住到谢玉非家里了。他给于淑钦发微信说要迟一两天回,于淑钦好像也没太意外,只回了他一条微信说:“就你贱,他家有什么好住的?”话里明显带着怨气。他来福州,于淑钦以为真的是探表弟的病,什么病她都懒得问。于淑钦只见过谢玉非一次,是八年前结婚不久,赵定力带她进城去谢家大院,算串个门认个亲。刚迈进去时,于淑钦还是很恭谦的,笑得老老实实,但很快笑就凝固住了。谢玉非根本没拿正眼瞧她,陈小娥更没有。作为主人,他们虽然都客气地招呼坐招呼喝茶招呼午饭,但脸都只冲着赵定力,话当然也定向说给赵定力听。也就是说谢玉非和陈小娥欢迎的是表哥赵定力,而作为表嫂的于淑钦,却一星半点的尊重都没得到。谢玉非后来把自己的想法私下告诉了赵定力,他的意思是,即使是这么大年纪了,再婚仍然是值得鼓励的,但如今又不是从前,无论如何都不该再把门槛降得这么低吧?凑合真没必要啊。女人多如牛毛,怎么能把文化程度这么低、看着又这么土气的女人娶进门?好歹谢家当年在福州城里也算一户掷地有声的豪门啊。赵家不是谢家,但至少算半个谢家,怎么说也是家门被辱了。
谢玉非又说:“我老婆也这么认为。”
单单自己的表哥不满就算了,陈小娥是外人,怎么轮得到她说三道四?赵定力当时嗯嗯几声忍下,明白这些话很得罪人,他必须全部吞在肚子里消化掉,但某次闲聊时,不知怎么还是嘴一松就和盘对于淑钦说了出来。一说完他当即就后悔了,但话既然已经出口了,就无法追回来。于淑钦脸马上拉长了,翻出白眼,重重地骂道:“放他妈的狗屁!”
她先是用重庆老家话骂,又用福州话重复了一句。在于淑钦没娶进门之前,赵定力完全没有想到女人竟能有这么大的嗓门,平日里,哪怕喊吃饭,门板似乎都会被震得颤动起来。一开始真不习惯,但慢慢他就无所谓了,是耳朵先开始适应,然后他觉得这样也好。乌瓦大院已经安静了这么多年,太静了,终于有一个女人来了,声音以一当十,把闲适太久的屋檐门板震一震,人气就不免涌了出来,从这一点看,意思还是有一点的。
那次之后于淑钦再没去过谢玉非家。所以赵定力说要去福州探望谢玉非,于淑钦是不以为然的。一个当医生的人需要你一个乡下人探病?于淑钦嘴一撇,一脸都是不高兴。赵定力没顾得上她高不高兴,他是为自己去的,每天活在七上八下中,他不去不行。
谢玉非开的药叫“甘露醇”,自色粉末状的。谢玉非说已经约好,肠镜明天就查,得把药先喝下清肠。家里号铝合金锅被拿出来,泡上开水,晚上喝下一大锅后,拉了一夜。本来凌晨还得再喝一锅,然后再拉,再然后就是一大早坐谢玉非的车一起去医院,进人检查室。但早上赵定力独自走了,他没有把另一锅药水喝下。
别墅共两层,谢玉非和陈小娥睡楼上主卧,赵定力睡楼下客房。与主人隔开一层楼板,倒让人松弛了很多,但赵定力哪里睡得着?上一趟刚拉好,转眼又急急坐到马桶上了,裤子像手风琴似的拉上折下,一波未消一波又起。这些日子他就是因为拉稀拉怕了,才进城找谢玉非,哪想到谢玉非给他药,让他这一夜肚子像一池堆满鱼的水,反复咕噜闹腾。他腿发软,不敢再喝,也不想查了。查就能查出是与非?即使查出了,接下去怎么办?开刀、化疗、没完没了地吃药……这么一想,心就荡到半空。趁着谢玉非夫妻还睡着,他在马桶旁抽了一大把卫生纸出了门。走之前他留下一张字条:“我先回家去。抱歉打扰你们了。”
天还没亮,到处都很安静,没人,没车。昨天坐谢玉非车从医院到这里,车拐进小区前,他往窗外看,恰好就看到路边戳着一幢斜屋顶的房子,外面挂着WC的标志。当时谢玉非还跟他炫耀,说这一带别看离市中心远,但市政设施已经很到位,你看连公共厕所都弄得这么漂亮了。赵定力出了大门,保安警觉地盯他看几眼,他屏住气,把身子挺了挺走过保安岗,然后找到厕所,确实漂亮,外型也跟一座小别墅似的。他在厕所后面的草丛里坐下,肚子还在响,仿佛一台热闹的戏正在里头开唱,他什么都不能做,只能老实守着这个漂亮的WC,随时一跃而起,大跑几步,朝着蹲位火速褪下裤子。
这些日子,拉稀对他是件多么习以为常的事,他的肚子成了一台高速运转的造屎机器,哪想到喝下谢玉非开的那一大锅药水后,他才领教了拉稀的真正伟力——每根肠子都像安上了抽水泵,马达开足,轰鸣震天。他低头看看自己的肚子,瘪瘪的,没有任何肚腩,它究竟靠什么藏得下这么多的屎?而且居然这么臭,是几十年老粪坑被使劲搅动之后才会有的那种恶狠狠的腐臭味。他揉揉肚子,如果屎这么多是个意外,那么肚子密封性这么好是更大的意外。屎关在肚皮里平时含而不露,一旦冲出来,竟然如此刺鼻。
所有香的东西吃下去,经过一个肚子,为什么竟臭成这样?
太阳起来了。太阳升高了。太阳弱下去了。肚子终于也慢慢消停下来,这期间他进出厕所共六次,有时拉多些,伴随着不绝的响声呈喷射状,有时好半天才安慰性地勉强挤出一点;有时肚子揪起,仿佛要滂沱,结果蹲半天却毫无建树。世界这么大,但至少这一天,除了厕所,其他都跟他没有任何关系。竟然活成与屎奋斗,终于便意没有了,他一开始还不敢相信,踟蹰一阵,捧住肚子像是跟它商榷,确认后才敢离开,先拦的士,再转公交。无论如何也得走了,再迟点公交车就停了。
从城里去青江村不再像以前那样只能坐船,沿江而建的公路是四车道的,铺着沥青,因为黝黑显出几分厚道。公交车也早通了,车站在村口西侧。他下了车,沿着那条十几年前槟城华侨集资捐建的水泥路慢慢走到村东头,爬上坡,跨进乌瓦大院。这一整天除了在路边买一瓶矿泉水喝下外,他什么都没吃。其实他什么都不想吃,喉咙那里像谁用塞子堵酒瓶似的,嵌下一个大塞子,气都喘不过来,哪里
— 没有更多了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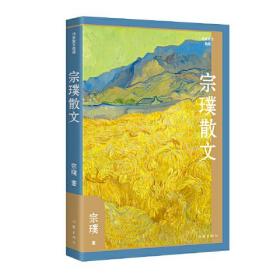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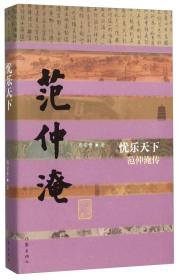

以下为对购买帮助不大的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