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正版现货新书 雪夜来客 9787559641212 冯骥才
全新正版现货,以书名为准,放心购买,购书咨询18931383650朱老师
¥ 30.49 5.2折 ¥ 59 全新
库存17件
北京丰台
认证卖家担保交易快速发货售后保障
作者冯骥才
出版社京华出版社
ISBN9787559641212
出版时间2020-07
装帧精装
开本32开
定价59元
货号1202052170
上书时间2024-10-13
- 在售商品 暂无
- 平均发货时间 9小时
- 好评率 暂无
- 最新上架
商品详情
- 品相描述:全新
- 商品描述
-
作者简介
冯骥才,浙江宁波人,1942年生于天津,中国当代作家、画家和文化学者。
25岁时,开始经历“十年”的磨难,生活及工作颠簸多变,做过工人、产品推销员和美术教师等。生活事业豁然开阔,曲折艰辛亦增见识,人生百味俱得心尝。由于深感于千万人命运的苦乐,遂立志于文学。主要著作有《珍珠鸟》《俗世奇人》《雕花烟斗》《高女人和她的矮丈夫》《三寸金莲》等。
目录
上编人间悲喜
木佛
雕花烟斗
炮打双灯
神鞭
中编百姓世相
胡子
雪夜来客
老夫老妻
楼顶上的歌手——一个在极度压抑下浪漫的故事
抬头老婆低头汉
高女人和她的矮丈夫
下编江湖传奇
黄金指
一阵风
燕子李三
四十八样
刘道元活出殡
小杨月楼义结李金鏊
内容摘要
在半个世纪的文学创作历程中,冯骥才的小说大多围绕着天津卫展开,含蕴着浓郁的津味津韵。本书篇目由冯骥才先生亲自甄选、修订,分为“人间悲喜”、“百姓世相”、“江湖传奇”三大编目,囊括了他创作至今的一系列代表作:《神鞭》(冯骥才从伤痕文学跳到文化小说的个深深的“足痕”)、《炮打双灯》(人间的苦乐唯有自知)、《雪夜来客》(大雪覆盖了他的脚印,是他留给我的很充实的空白)、《楼顶上的歌手》(一个在靠前压抑下浪漫的故事),以及“第七届鲁迅文学奖”获奖作品《俗世奇人》中的经典篇目;本书还特别收录了冯骥才全新小说《木佛》——一段木头的奇遇,揭开一个隐秘而荒诞的世界。冯骥才特为本书撰写序言,与读者畅谈“作品的生命”。
说尽市井烟火中的奇人奇事,遍观津门大地上的绝招绝活!让我们一同走进冯骥才的大千世界,见证和感受人世间的每一寸喜悦和悲辛。
创作脉络。
主编推荐
★有名作家冯骥才近期新小说集,执笔50年小说精粹。★冯骥才亲笔作序,畅谈“作品的生命”。★定制收录冯骥才2020近期新小说《木佛》+创作手记。★冯骥才亲自审定篇目并做修订。★精装典藏,高品质阅读。
精彩内容
\\\\\\\\\\\\\\\\\\\\\\\\\\\\\\\\\\\\\\\\\\\\\\\\\\\\\\\\\\\\\\\"木?佛先别问我叫什么,你慢慢就会知道。
也别问我身高多高,体重多少,结没结婚,会不会外语,有什么慢性病,爱吃什么,有没有房子,开什么牌子的车,干什么工作,一月拿多少钱,存款几位数……这你渐渐也全会知道。如果你问早了,到时候你会觉得自己的问题很可笑,没知识,屁也不懂。
现在,我只能告诉你,我看得见你,听得见你们说什么。什么?我是监视器?别胡猜了。我还能闻出各种气味呢,监视器能闻味儿吗?但是,我不会说话,我也不能动,没有任何主动权。我有点像植物人。
你一定奇怪,我既然不能说话,怎么对你说呢?
我用文字告诉你。
你明白了—现在我对你讲的不是语言,全是文字。
你一定觉得这有点荒诞,是荒诞。岂止荒诞,应该说极其荒诞。可是你渐渐就会相信,这些荒诞的事全是真事儿。
一
我在一个床铺下边待了很久很久。多久?什么叫多久?我不懂。你问我天天吃什么?我从来不吃东西。
我一直感受着一种很浓烈的霉味。我已经很习惯这种气味了,我好像靠着这种气味活着。我还习惯阴暗,习惯了那种黏糊糊的潮湿。唯一使我觉得不舒服的是我身体里有一种肉乎乎的小虫子,在我体内使劲乱钻。虽说这小虫子很小很软,但它们的牙齿很厉害,而且一刻不停地啃啮着我的身体,弄得我周身奇痒难忍。有的小虫已经钻得很深,甚至快钻到我脑袋顶里了。如果它们咬坏了我的大脑怎么办?我不就不能思考了吗?还有一条小虫从我左耳朵后边钻了进去,一直钻向我的右耳朵。我不知道它们到底想干什么,我很怕叫它们咬得千疮百孔。可是我没办法。我不会说话、讨饶、呼救;我也不知向谁呼救;不知有谁会救我。谁会救我?
终于有一天,我改天换地的日子到了!我听见一阵很大的拉动箱子和搬动东西的声音。跟着一片刺目的光照得我头昏目眩。一根杆子伸过来捅我,一个男人的声音:“没错,肯定就在这床底下,我记得没错。”然后这声音变得挺兴奋,他叫道:“我找到它了!”这杆子捅到我身上,一下子把我捅得翻了一个儿。我还没弄清怎么回事,也没看清外边逆光中那个黑乎乎的人脑袋长得什么样儿,我已经被这杆子拨得翻过来掉过去,在地上打着滚儿,然后一直从床铺下边犄角旮旯滚出来,跟着被一只软乎乎的大手抓在手里,拿起来“啪”一声撂在高高一张桌上。这人朝着我说:“好家伙,你居然还好好的,你知道你在床底下多少年了吗?打‘扫四旧’那年一直到今天!”打“扫四旧”到今天是多少年?什么叫“扫四旧”,我不懂。
旁边还有个女人,惊中带喜地叫了一声:“哎呀,比咱儿子还大呢!”我并不笨。从这两句话我马上判断出来。我是属于他俩的。这两人肯定是夫妇俩。男人黄脸,胖子,肥厚的下巴上脏呵呵滋出来好多胡茬子;女人白脸,瘦巴,头发又稀又少,左眼下边有颗黑痣。这屋子不大,东西也不多。我从他俩这几句话听得出,我在他床底下已经很久很久。究竟多久我不清楚,也不关心,关键是我是谁?为什么一直把我塞在床底下,现在为什么又把我想起来,弄出来?这两个主人要拿我干什么?我脑袋里一堆问号。
我看到白脸女人拿一块湿抹布过来,显然她想给我擦擦干净。我满身灰尘污垢,肯定很难看,谁料黄脸胖子伸手一把将抹布抢过去,训斥她说:“忘了人家告诉你的,这种老东西不能动手,原来嘛样就嘛样,你嘛也不懂,一动不就毁了?”白脸女人说:“我就不信这么脏头脏脸才好。你看这东西的下边全都糟了。”“那也不能动,这东西在床底这么多年,又阴又潮,还能不糟?好东西不怕糟。你甭管,我先把它放到柜顶上去晾着,过过风。十天半个月就干了。”他说完,把我举到一个橱柜顶上,将我躺下来平放着,再用两个装东西的纸盒子把我挡在里边。随即我便有了一连许多天的安宁。我天性习惯于安宁,喜欢总待在一个地方,我害怕人来动我,因为我没有任何防卫能力。
在柜顶上这些日子我挺享受。虽然我看不见两个主人的生活,却听得见他们说话,由他们说话知道,他们岁数都大了,没工作,吃政府给贫困户有限的一点点救济。不知道他们的孩子为什么不管他们。反正没听他们说,也没人来他们家串门。我只能闻到他们炖菜、烧煤和那个黄脸男人一天到晚不停地抽烟的气味。我凭这些气味能够知道他们一天只吃两顿饭。每顿饭菜都是一个气味,好像他们只吃一种东西。可是即便再香的饭菜对我也没有诱惑—因为我没有胃,没有食欲。
此刻,我最美好的感觉还是在柜顶上待着。这儿不阴不潮,时时有小风吹着,很是惬意。我感觉下半身那种湿重的感觉一点点减轻,原先体内那些小虫子好像也都停止了钻动,长久以来无法抗拒的奇痒搔心的感觉竟然消失了!难道小虫子们全跑走了?一缕缕极其细小的风,从那些小虫洞清清爽爽地吹进我的身体。我从未有过如此美妙得近乎神奇的感觉。我从此能这么舒服地活下去吗?
一天,刚刚点灯的时候,有敲门声。只听我的那个男主人的声音:“谁?”门外回答一声。开门的声音过后,进来一人,只听我的主人称这个来客为“大来子”。过后,就听到我的男主人说:“看吧,这几样东西怎么样?”我在柜顶上,身子前边又有纸盒子挡着,完全看不到屋里的情景。只能听到他们说话。大来子说话的腔调似乎很油滑,他说:“你就用这些破烂叫我白跑一趟。”我的女主人说:“你可甭这么说,我们当家的拿你的事可当回事了。为这几样宝贝他跑了多少地方搜罗,使了多少劲,花了多少钱!”“我没说你当家的没使劲,是他不懂,敛回来的全是不值钱的破烂!破烂当宝贝,再跑也是白跑!”女主人不高兴了,她呛了一句:“你有本事,干吗自己不下去搜罗啊。”大来子说:“我要下去,你们就没饭吃了。”说完嘿嘿笑。
男主人说:“甭说这些废话,我给你再看一件宝贝。”说完,就跑到我这边来,蹬着凳子,扒开纸盒,那只软乎乎的大手摸到我,又一把将我抓在手里。我只觉眼前头昏目眩地一晃,跟着被“啪”的一声立在桌上—一堆瓶瓶罐罐老东西中间。我最高,比眼前这堆瓶子罐子高出一头,这就得以看到围着我的三个人。除去我的一男一女两主人,再一位年轻得多,圆脑袋、平头,疙疙瘩瘩一张脸,贼乎乎一双眼,肯定就是“大来子”了。我以为大来子会对我露出惊讶表情,谁料他只是不在意地扫我一眼,用一种蔑视的口气说:“一个破木头人儿啊!”便不再看我。
由此,我知道自己的名字—木头人。
随后我那黄脸的男主人便与大来子为买卖桌上这堆老东西讨价还价。在男主人肉乎乎的嘴里每一件东西全是稀世珍奇,在大来子刁钻的口舌之间样样却都是三等货色,甚至是赝品。他们只对这些瓶瓶罐罐争来争去,唯独对我提也不提。最后还是黄脸男主人指着我说:“这一桌子东西都是从外边弄来的,唯独这件是我祖上传下来的家藏,至少传了四五代,打我爹记事时就有。”“你家祖上是什么人家?你家要是‘一门三进士’,供的一准都是金像玉佛。这是什么材料?松木桩子!家藏?没被老鼠啃烂了就算不错。拿它生炉子去吧。”我听了吓了一跳。我身价原来这么低贱!说不定明天一早他们生炉子时就把我劈了、烧了。瞧瞧大来子的样子,说这些话时对我都不再瞅一眼,怎么办?没办法。我是不会动的。逢此劫难,无法逃脱。
最后,他们成交,大来子从衣兜里掏出厚厚一沓钱,数了七八张给了我的男主人。一边把桌上的东西一件件往一个红蓝条的编织袋里装,袋里有许多防压防硌的稻草。看他那神气不像往袋子里装古物,像是收破烂。最后桌上只剩下我一个。
女主人冲着大来子说:“您给这点钱,只够本钱,连辛苦费都没有。当家的—”她扭过脸对男主人说,“这种白受累的事以后真不能再干了。”大来子眨眨眼,笑了,说:“大嫂愈来愈会争价钱了。这次咱不争了,再争就没交情了。”说着又掏两张钱,放在女主人手里,说,“这辛苦费可不能算少吧。”说着顺手把孤零零立在桌上的我抄在手里,边说,“这破木头人儿,饶给我了。”男主人说:“这可不行,这是我家传了几代的家藏。”伸手要夺回去。
大来子笑道:“屁家藏!我不拿走,明天一早就点炉子了。怎么?你也想和大嫂一样再要一张票子。好,再给你一张。大嫂不是不叫你收这些破瓶烂罐了吗?打今儿起我也不再来了。我没钱干这种赔钱买卖!”说完把我塞进编织袋。
我的黄脸主人也没再和大来子争。就这样,我易了主,成了大来子的囊中之物了。
我在大来子手中的袋子里,一路上摇来晃去,看来大来子挺高兴,嘴里哼着曲儿,一阵子把袋子悠得很高很带劲,叫我害怕他一失手把我们这袋子扔了出去。但我心里更多的是庆幸!多亏这个大来子今天最后不经意地把我捎上,使我获救,死里逃生,没被那黄脸男人和白脸女人当作糟木头,塞进炉膛烧成灰。
可是,既然我在大来子眼里这么差劲,他为什么要捎上我,还多花了一张票子?\\\\\\\\\\\\\\\\\\\\\\\\\\\\\\\\\\\\\\\\\\\\\\\\\\\\\\\\\\\\\\\"
媒体评论
冯骥才的作品我读的多了,长短篇的小说和散文。——冰心
大冯从精神上更像是个孩子,他懂得尊重别人,这正是他的魅力。——王蒙
他是一个真正的“俗世奇人”,他好像是有很多的手、很多的腿,不然怎么能做那么多的事情?——张抗抗
大家看这个“骥”字:首先一个“马”,马不停蹄地奔波;上面是一个“北”,天津大学原为北洋大学;很底下是一个“共”,公共事务的“共”;很核心在于中间的“田”,他从未离开过这块土地。——白岩松
— 没有更多了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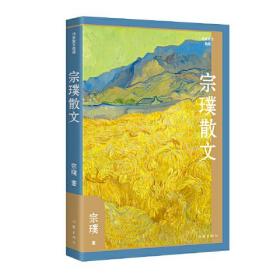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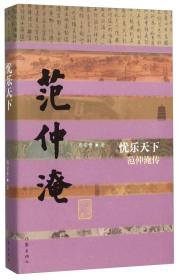

以下为对购买帮助不大的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