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著名中学师生推荐书系·沧桑无语
正版全新
¥ 15.96 6.4折 ¥ 25 全新
库存11件
上海浦东
认证卖家担保交易快速发货售后保障
作者王充闾 著,张书婷 编注
出版社东方出版中心
ISBN9787547302255
出版时间2019-09
装帧其他
开本32开
纸张胶版纸
定价25元
货号1317894
上书时间2024-05-21
- 在售商品 暂无
- 平均发货时间 7小时
- 好评率 暂无
- 最新上架
商品详情
- 品相描述:全新
- 商品描述
-
【书 名】 著名中学师生推荐书系·沧桑无语
【书 号】 9787547302255
【出 版 社】 东方出版中心
【作 者】 王充闾 著,张书婷 编注
【出版日期】 2019-09-01
【版 次】 1
【开 本】 32开
【定 价】 25.00元
【编辑推荐】
人文与语文的有机结合
提高中学生的语文素养与考试成绩
多位中学语文特级教师鼎力推荐
中学生核心素养拓展必备读本
1 “著名中学师生推荐书系”是东方出版中心推出的名牌系列产品,在中学师生中享有“优秀语文教辅”声誉。本书是2019年修订版。
2编写者都是教学*线、经验丰富的中学语文资深教师。
3 名师导读与点评有机结合,提高中学生的语文素养与考试成绩。
4大作家小经典 引导学生进入文学的殿堂。
【内容简介】
在《沧桑无语》中,作者实实在在地把眼光转向了过珐的岁月,倾注于历史的风云和生命的来路。以雄浑沉着的绘景笔致,开掘山水之间的历史意蕴,将零编片简、断瓦残碑装订成新的史册;在敏锐的思辨之中,以冷隽深邃的史家目光审视存在的价值,诠释人生哲理意趣,体验审美情境。
【目录】
目录
编注者说
第*单元 千秋叩问
终古凝眉
梦寻
春梦留痕
叩问沧桑
千载心香域外烧
单元链接
第二单元 山水追梦
青山魂
寂寞濠梁
凉山访古
桐江波上一丝风
单元链接
第三单元 红尘解悟
当人伦遭遇政治
用破一生心
守护着灵魂上路
九一八,九一八
单元链接
编后语
【文摘】
凉山访古
一
凉山彝族自治州的首府西昌,(西昌位于四川省西南部安宁河谷地区。)古称邛都。这在《史记·司马相如列传》中,早有记载。
原来,司马相如(司马相如(约公元前179年—前118年),字长卿,成都人,西汉辞赋家,其代表作品为《子虚赋》。)对于开发祖国西南边疆,促进这一带少数民族地区同中原腹地的经济、文化交流,做出过重要的贡献。可是,过去人们只知道他是一位才华盖世、辞赋出色当行的文学大家,又是一个“忒煞情多”(出自元代诗人赵孟頫的《我侬词》:“你侬我侬,忒煞情多,情多处,热如火。)的风流种子。他曾偕同美女卓文君私奔,家贫,文君当垆卖酒,相如着犊鼻裩涤器于市,(犊鼻裈(dú bí kūn),亦作"犊鼻裩"。省作"犊鼻"、"犊裩"。 意为短裤。涤(dí笛):洗刷。指司马相如洗刷酒器。后以此典比喻文人寒士贫困落魄。)传为千古风流韵事。他还替那位被打入冷宫的陈皇后写过一篇《长门赋》,希望引起汉武帝重念旧情,回心转意。为此,作赋人得到了百斤黄金的酬报。寥寥千余字,却换来这么多的金子,这个“润笔”可不算低了,只是,那篇赋却并未取得预期的效果。
我们且把时光拉回到公元前130年(西汉元光五年)。当时,汉武帝派遣唐蒙出使夜郎(今贵州西部一带)。这是僻处西南边疆的一个部族,四周高山环绕,与中原素无来往。部族首领竹多同从来没有到过其他地方,根本不了解外面的世界,以为夜郎是天底下*大的国家。当下便问唐蒙:“你们汉朝,有我们夜郎大吗?”从此留下了“夜郎自大”的话柄。及至他们见到唐蒙带来的丰盛礼品,才大开了眼界。唐蒙乘便宣传了汉朝的地大物博,文明强盛,使夜郎及其附近的诸多部落深感向慕,表示愿意归附。
签订了盟约之后,唐蒙返回长安,向武帝报告了结交夜郎等部族的经过。武帝便把这些地方改为犍为郡,并指令唐蒙负责修筑一条通往这些地方的大路和栈道。为此,唐蒙在巴蜀地区大肆征集人力。由于工程浩大而且艰巨,士兵和民夫死伤了不少,一时谣言四起,蜀郡民众纷纷出逃避难。消息传到朝廷,汉武帝便派遣以《子虚》、《上林》两赋受到赏识的司马相如为特使,前往安抚百姓,纠正唐蒙的阙失。
司马相如入蜀后,写了一篇《喻巴蜀檄》,讲明朝廷沟通“西南夷”和筑路的意义,说这是从整个国家利益出发,为了解决“道里辽远,山川阻深”的困难。而唐蒙的一些做法,“皆非陛下之意”,希望各地仰体圣衷,免除惊恐。司马相如是个有心人,在妥善处理这起案件,圆满完成出使任务的同时,顺便对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的情况及其与内地的关系,作了比较详尽的调查。
夜郎的归附产生了很好的影响,邛都、笮都(今四川西昌及雅安、汉源一带)的一些部落也都想比照夜郎的待遇归附称臣。当时,对于“沟通西南夷”是否必要,朝中一班人的看法并不一致,汉武帝首先征询了司马相如的意见。相如胸有成竹地回答说:邛、笮等地和蜀郡(今成都)相去不远,道路也不难打通。那里,秦代曾置为郡县,到本朝建国时才罢除。现在,若能再度与之沟通,进而设郡置县,其价值是远胜“南夷”诸国的。汉武帝听了,深以为然,便拜封司马相如为中郎将,委之以全权处理有关“西南夷”事务的使节重任。
司马相如带着一批助手,很快地来到今四川西部、南部少数民族地区,与当时的邛、笮、冉、骁、斯榆等部落,进行了广泛的交往,各少数民族部落的首领都表示愿意归附汉朝。从而撤去了旧时的边关,西边以沫水、若水为界,南边扩大到牂牁,打通了零关道,修筑了孙水桥。“还报天子,天子大悦。”紧接着,汉朝就在这里设置了十几个县,全部隶属蜀郡。
相如出发前,曾针对蜀地父老和某些朝廷大臣反对开通西南边疆的意见,写过一篇《难蜀父老》的辩难文字,假托有27名荐绅缙绅。(荐,通“ 缙”。指有官职或做过官的人。)、耆老对“通西南夷”提出责难,从而引出作者的正面阐释与答辩。文中阐明了这一举措的深远意义,同时,对外宣扬了西汉王朝的偃甲兵、息诛伐、德泽广被、教民化俗的政策,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二
从这里可以知道,早在2100多年前 ,大、小凉山一带即已划入中央政府的辖区,此间住着彝(当时称“夷”)、汉、藏等民族,此其一;其二, 封建王朝对于少数民族的策略是“羁縻勿绝”,即只在牵制而并非灭绝;其三,凉山地区处于西南边疆的要冲,自古就形成了“邛通则路通,邛阻则路阻”的局面。
因此,打通凉山,历朝历代都受到官府和民间的重视。其地与蜀郡的沟通,尽管官方往来“至汉兴而罢”,但民间商贾贸易始终未曾隔断,并不是“尔来四万八千岁,不与秦塞通人烟”。先后开通的邛笮道、牦牛道、清溪道、西川道等,尽管称谓不同,但其为横跨大、小凉山的通道则无异。它们北接巴蜀,南连滇越,*后全部汇入古代有“南方丝路”之誉的“蜀身毒道”。
说到南方丝绸之路,人们会联想到那条东起长安,经河西走廊通往中亚、西亚以及欧洲、北非的西北丝绸之路;记起那位与司马相如同时代的“凿空”西域、开拓中西交通的先驱者张骞。
这位2000多年前的伟大的外交家、探险家,曾两次出使西域,以其不畏艰险、不怕牺牲的精神,为加强我国各民族的联系,促进民族间的融合,扩大中外友好往来,经略西部疆域,耗费了毕生的精力。这是许多人都知道的。但是,对于他还曾为开发祖国西南边疆,特别是疏通南方丝绸之路做过贡献这一点,知道的恐怕就不是很多的了。
据《史记·西南夷列传》和《大宛列传》记载,张骞第*次出使西域归来后,于西汉元狩元年(公元前122年)曾对汉武帝讲,他在大夏国(今阿富汗一带)见到过蜀地生产的麻布和邛都之竹所作的手杖,询其来路,据云乃当地商人从身毒(今印度、巴基斯坦、孟加拉一带)身毒(依照古语发音接近"sin do" 或 "shin do"),直至今日在中国南方一些方言(例如闽南语)仍保留了这种发音。这是华夏文明古代对印度地区的称呼之一。采购的。大夏国位居中国西南,距离约一万二千里,身毒又在大夏东南数千里。此间既然有蜀地产物,推想自“西南夷”地区通往身毒,路程一定不会太远。鉴于西域一路险阻颇多,建议打通从巴蜀经“西南夷”地区直通身毒、大夏的通道。汉武帝当即采纳了这个意见。派遣使官十余人,带着财物,分四路深入蜀西南地区,探寻通往身毒的道路。可惜,多次派出的使者,均在现今的云南大理一带受阻,*后无功而还。
继张骞之后,杰出的军事家班超先后在西域奋斗三十一载,巩固了东汉在西域的统治,维护了祖国的统一。
无独有偶,与两位军事家开发西域相对应,经略西南边疆的,竟是两位杰出的文学家。踵步司马相如后尘,西汉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伟大的史学家司马迁以汉武帝侍从官身份,奉命出使邛、笮 、昆明等地,既建立了事功,又掌握了西南各少数民族的大量资料,为日后撰写《西南夷列传》创造了条件。
看来,武将和文人不仅功业迥然不同,而且,“鸿爪留痕”也大相歧异。也许真的应了“千秋定国赖戎衣”这句话,西域沟通之后,同中原地区的经济、文化交流日益频繁,内地的先进生产技术在西域得到广泛推广,丝绸、漆器等大量手工业品源源流入西域;同时,西域的葡萄、苜蓿、胡萝卜以及骆驼、良马等物种也传入内地,尤其是那里的音乐、舞蹈,对汉民族文化的发展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相比之下,西南边疆地区的发展及其与内地的联系就差得太远了。由于交通阻塞,那里并未从根本上扭转其封闭状态。结果,在西北丝绸之路上,张骞有碑,班超有城,青史标名,万人仰颂。可是,在西南地区却没有见到过“两司马”的任何遗迹。当然,他们“寄身于翰墨,见意于篇籍,不假良史之词,不托飞驰之势,而声名自传于后”(曹丕语),又是张骞、班超所望尘莫及的。这也就是“英雄儿女各千秋”吧?
三
中国作家采风团一行,这次来到凉山彝族自治州,许多人都是首途,因此,稍事休息,便集聚在一张四川省地图的前面,听当地一位彝族文友介绍有关情况。这位文友指着地图西南部一片广阔的地域,说,凉山是全国*大*集中的彝族聚居区,与西藏有些相似,是一片神奇古老、峻丽多姿,承载着无数自然与人文奥秘的土地。
这里,地处云贵高原与四川盆地之间的过渡地带,北部、东部和南部为水深流急的大渡河、金沙江迂回环绕,境内有小相岭、碧鸡山、黄茅埂纵横盘错,其间高山耸峙,河川割裂,峡谷幽深,地形陡峭,加上旧时代彝族“家支”势力的割据,历代反动统治阶级的禁锢、封锁,使整个凉山地区与外界的交往受到重重阻隔,长期处于封闭状态。
有一首民谣记述了这种封闭、隔绝的实况:
上山入云间,下山到河边。
山前能对话,相见走一天。
大诗人李白曾经苦吟:“见说蚕丛路,崎岖不易行”;“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而旧日的凉山,道路之难行,在蜀道中又是数一数二的。过去奴隶娃子被抓进凉山去,叫做“青蛙掉进井里”,永世没有逃出之日。有的地方耕牛无法进去,只好背运牛犊进山养大,以解决耕作之需。由于交通阻塞,致使日用消费品奇缺,老阿妈买一枚缝衣针要从鸡窝中摸出十个鸡蛋来交换,而猎手们鸡蛋大的一块麝香也只能换回一斤白酒。
封闭当然是坏事,但对自然生态环境和人文景观也有一定的保护作用。在举世进入现代文明时代,又苦于“文明病”折磨、困扰的时候,凉山却为我们提供了一方净土,托出了一块充满着迷人景色、绮丽风光的胜地,保留了人类*古朴、*浓烈、*独特的文化传统和民风民俗。
这里,有四川*大的淡水湖邛海,《马可·波罗游记》中称它为珍珠湖。作者记述说:“湖中珍珠无数”,“然大汗不许人采取”,否则,“珠价将贱,而不为人所贵矣”。
“清风、雅雨、西昌月”,为川西南三大景观,其中的“邛池夜月”,天下驰名,因而,西昌获得了“月城”的美称。原来,这里地处横断山脉西缘,海拔高而纬度低,四面青山环绕,中部是安宁河平原地带,属于干湿交替的亚热带季风气候,常年风轻云淡,晴好天气极多,加上山林和湖水对大气层的过滤,使这里的月光分外皎洁。古人有诗赞曰:
天空临皓月,海上*分明。
境过银河界,人来水廓城。
在“月亮的女儿”青铜雕塑下面,彝族金融家、诗人阿卓哈布给我们讲了一个美丽的传说:
在大凉山领扎洛这个山清水秀的地方,有一个心灵手巧的彝家姑娘,名叫兹莫领扎。她放牧的牛羊长得又肥又壮,她种的荞麦年年获得丰收,她唱的歌声传遍了天涯海角,她织的羊毛披毡上现出一个逼真的世界:她织上了花,花儿招来蝴蝶;织上了蜜蜂,蜜蜂引来布谷;织上了贝母鸡,贝母鸡会请来公山羊;织上了神龙鹰,神龙鹰便驮来一个绚丽的春天。
月宫仙女听到这个信息后,便派出七彩云霞去寻访,想要请兹莫领扎来教她织披毡。先是派乌云,找遍了大小山沟,没见踪影;又派出黄云、绿云、蓝云,找遍了山林、草坡和村庄,还是没有找到;*后派出眼明心亮的白云,才在领扎洛山的古松下找到了,兹莫领扎姑娘正在织美丽的披毡。于是,她踩着七色云霞搭成的虹桥来到了桂殿仙宫,朝朝暮暮教月宫仙子织披毡、弹月琴。……
西昌城南三十公里外有一座螺髻山,海拔4300多米,为250万年前第四纪古冰川运动的遗世杰作,保存有完整清晰的大型冰川刻槽,具有极高的科学研究和旅游观赏价值。山上“烟中鬓髻,尚觉模糊,雨际青螺,偏多秀媚”。自古即有“十二佛洞、十八顶、二十五坪、三十二天池、一百单八景”,令人悠然神往。红、橙、黑、黄、酱、绿等各色海子点缀山中,传说是仙妃沐浴的地方,日月朗照,宛如熠熠闪光的一颗颗宝石镶嵌在白云深处。山中有许多特异景观,诸如冰化源泉、露零芳草、水磨奇石、烟飞林箐,均为世所称道。
怪不得明朝进士马忠良在游记中要说:“螺髻山开,峨眉山闭。”意思是,如果有朝一日,这里能够开发出来,那时,秀出西南、誉满寰中的峨眉山,就将大为逊色,只好悄然关闭了。
四
凉山地区的人文景观,更是独具特色,多彩多姿。神秘的原始宗教,五光十色的服饰,优美动人的舞蹈,以及“恒河沙数”的神话、故事、歌谣,都具有神奇的魅力和恒久的诱惑力。特别是人类*后一块母系社会的遗址泸沽湖,那里的充满传奇色彩的东方“女儿国”和摩梭人奇特、浪漫的“阿肖”走婚风俗,吸引着五洲四海的万千游人和中外众多的作家、学者。
沪沽湖养育的摩梭女儿,个个美丽健壮,勤劳善良,情深似海。她们不奢求不属于自己的一切,不会做金钱、物欲、权势的奴隶。她们按照质朴的本性,遵循自己心灵的指引,无忧无虑地劳动、生活、爱恋着。在她们的头脑里,没有古圣先贤留下的礼教、清规,没有“所适非偶”的烦恼、忧伤。她们在属于自己个人所有的花房里编织着少女的梦,品啜着情真意挚的爱的琼浆。
当地文友介绍说,许许多多前来采风的作家、艺术家、新闻记者和民俗学家,对于这里的婚姻生活都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有的还写出了动人心弦的文艺作品,或者完成了专门的学术报告。听到这里,同行的一位学者神秘地问我:“你认为这里有什么道理?”我猜想,他一定会有一番妙论,便笑着说:“我愿洗耳恭听。”
他说,人们到一个地方游览,如同阅读文学作品一样,都会将自己的感受或者思索,不自觉地对象化——即化入到那种地域、那部作品的情境框架中去,设身处地,比较一番。也就是,在审美的返照中,完成对自身的观照、对比与衡量。有价值的地方风物,优秀的文学作品,它的感召力、生命力,就在于能够提供一种契合其文化心态,满足其欲望要求的“对象化的相关物”。具体说到沪沽湖的“走婚”形式上,其实,人们与其说是在看人家,不如说是在想自己——希望自己也有这样一种自由选择的条件。他们是在向往一种世外桃源,一种诗意人生。从这个意义上说,他们是到这里来寻梦,寻找自己已经失落了的梦境,——梦是愿望的达成,是现实生活中某些缺憾的一种补偿。尽管梦终归也要醒,但梦本身,难道不是一种生活吗?它和实际生活的区别,只在于虚实、长短而已。
我觉得,他说得很妙。
凉山彝族自治州所属的广大区域,是以彝族为主体,彝、汉、藏、回、蒙等十几个民族,经过几千年的奋斗,共同开发拓展出来的。
彝族在旧时史籍中称做“夷人”、“倮族”,而彝民自称为“诺苏”。解放以后,根据广大彝族民众的意愿,以鼎彝之“彝”作为统一的民族名称。多种学科的材料证明,彝族先民是以自西北而南下的古羌人部落为基础,在西南的川、滇交接带的金沙江两岸,融合了当地众多的土著部落而逐步形成的。凉山彝族的直系祖先,按照彝族民间普遍传说,则为古侯、曲涅两个原始部落,大约在西汉时期即由今云南昭通一带陆续迁入大、小凉山。自唐代以迄明清,黔西、滇东北的彝民又有过数次大规模的迁入。
这里的汉族居民大多数迁自内地,或为封建王朝屯垦戍边,或自发地到这里来落脚谋生,*早的亦有两千多年的历史。这是一个典型的农耕族群,他们以土地为核心,建造了区别于其他民族的社会经济形态。
在漫长的岁月中,彝族人民创造了灿烂的民族文化,并且,小心翼翼地接受其他民族一些生产技术与管理方式;同时,以血缘家支联盟为依托,注意加强内部的凝聚力,抵御着外来文化的冲击。但是,由于地处青藏高原、云贵高原和四川盆地汇接地带,又不能不受到来自北部和西部草原牧业文化的熏陶,东部巴蜀文化的哺育,以及东北部江汉流域稻田耕作文化的幅射,因而表现出多源、共生的特点。
大、小凉山是一个早已闻名于世的特殊的民族文化区域,是20世纪初以来中外人类学、民族学、历史学研究的一个热点。其原因,就在于此间虽然处在人口稠密、历史文化悠久的东亚中部的内陆,与素称“天府之国”的人文荟萃的成都平原近在咫尺,却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由于情况复杂的地理、人文环境等因素,形成了相当特殊的民族社会经济的发展样式,产生了一套以低需求适应低生产的社会文化机制。
而建立在生产水平低下和地理环境分散、封闭的基础之上的血缘组织——“家支”,以及“家支”之间的械斗,又使财富积累和扩大再生产受到严重影响,统一的政权组织无由建立。这样一来,凉山的社会发展就只能在原地上打转,结果形成了世界史上绝无仅有的凉山奴隶社会的“两千年一贯制”。
如果说,中华民族就整体来讲,是带着半封建、半殖民地的镣铐,迈着沉重的脚步,叩开20世纪大门的;那么,凉山彝家则是背负着奴隶制的枷锁,从长夜漫漫的历史隧洞中缓慢地走出来,比之整个中华民族,其步履无疑是更为沉重、更加艰难的。
五
彝族的创世史诗《勒俄特依》中说,彝族和汉族本是居木武吾的两个儿子,彝族儿子名叫武吾格自,挽起蒿草做地界,住在高山上;汉族儿子武吾拉业,垒起石块做地界,住在湖水边。那时候,水牛、黄牛并着走,耕作时在一起,休息时各走各。那时候,彝人也说汉话,汉人也留彝髻,彝、汉兄弟亲如手足,共同为开发八百里凉山抛洒汗水。这动人的神话传说,反映了两族人民的亲密关系和美好愿望。
但是,由于历代反动统治者实行民族歧视、民族压迫和民族隔离的政策,不断地对彝区进行剿灭、征服;而凉山彝寨的奴隶主为了维护其专制统治,转移斗争视线,又人为地制造民族矛盾,宣扬“石头不能当枕头,汉人不能搭朋友”,彝、汉两族的冲突也是经常的,带来了无边的历史性灾难。
当然,这种冲突和对立,在我国两千年的彝、汉民族史上,毕竟只是一股支流;而主流则是两族劳动人民共同的生产劳动、抗暴御侮,并肩保卫、建设祖国的西南边疆。
《西昌县志》记载,辛亥革命前夜,西昌地方官府横征暴敛,鱼肉人民。知县章庆以推行新政为名,增加苛捐杂税。贫民割一背草,只售二、三十文,要按十抽五;每碗茶原售三文,加厘捐后要售四文。弄得物价飞涨,民不聊生。当时,正值清政府邮传部大臣盛宣怀出卖筑路利益给外国银行团,原籍西昌的同盟会会员王西平和刘次平、朱用平(世称“三平先生”),发动群众响应成都的“保路运动”,开展抗捐、抗粮和反对教会势力的斗争,得到当地民团的支持。
团总张耀堂联合了安宁河两岸五千多彝、汉民众,趁着西昌清军外调,城防空虚,杀进城来。他们以捕获所谓“暴民”名义,伪将几名群众捆绑起来,由民团押送入城,邀功请赏,从而顺利地叫开了城门,攻占了县署,揪出知县章庆,立即斩首。知府王典章迫于形势,伪装支持民众,以温言软语将民团和起义群众骗出城池,然后立即紧闭四门,暗地纠结各地武装星夜驰援,并勾结教会势力,向义军大举进攻。起义失败后,王、刘、张三位组织者,连同义军一千余人惨遭杀害。但彝、汉等各族人民的反抗斗争迄未停止,一直到推翻清王朝的统治。
我们发现,在古代汉族官员中,彝家似乎对诸葛亮有特殊的好感,漫步山乡,常常听到一些彝族老人称之为“孔明先生”。蜀汉建兴年间,南中诸郡(今云南、贵州西部和四川西南一带)相继发生叛乱,为了安定后方,以图中原,诸葛亮亲率大军南征。出发前,曾任越嶲(辖今凉山一带)太守、熟悉南中情况的马谡相送数十里外,一再建言:“攻心为上,攻城为下;心战为上,兵战为下。愿早服南人之心,以收长治久安之效。”诸葛亮听了深以为然,南征中始终坚持这一战略方针。
阿卓哈布先生讲给我们说,当时,诸葛亮从成都出发,经过今宜宾的屏山、雷波的马湖,于卑水(今昭觉)与叛将高定决战,收复了越嶲郡;然后“五月渡沪(金沙江)”,在今云南曲靖一带俘获了孟获。为了使这位深为“夷、汉所服” 的彝族英雄心悦诚服,真心归顺
相关推荐
— 没有更多了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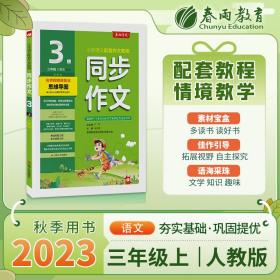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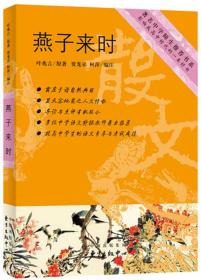
以下为对购买帮助不大的评价